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2017的末尾,講一著名的"人生意義"比喻:
Of Human Bonda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5 and considered Maugham’s masterpiece,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work that follows the life of protagonist Philip Carey. Born with a club foot, this memorable character enters the world not only deformed, but an orphan. As an adult, he aspires to be an artist in Paris, and then a doctor in London, struggling with money and love. At one point, his friend, Cronshaw, points him toward the meaning of life:
Of Human Bonda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5 and considered Maugham’s masterpiece,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work that follows the life of protagonist Philip Carey. Born with a club foot, this memorable character enters the world not only deformed, but an orphan. As an adult, he aspires to be an artist in Paris, and then a doctor in London, struggling with money and love. At one point, his friend, Cronshaw, points him toward the meaning of life: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Cluny, the museum? There you will see Persian carpets of the most exquisite hue and of a pattern the beautiful intricacy of which delights and amazes the eye. In them you will see the mystery and the sensual beauty of the East, the roses of Hafiz and the wine-cup of Omar; but presently you will see more. You were asking just now what was the meaning of life. Go and look at those Persian carpets, and one of these days the answer will come to you.”
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Memories Unburdened By Sorrow
這本書是"香港"譯界的國際、本土親友之情誼 (多為故人了)記錄,感人。
正式的"作者簡介"很重要:作者從小中英文好,中學時被黃兆傑先生的"萬世師表"的英譯的"蝴蝶效應"等,待入翻譯研究,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嫁老英,30歲起即主持《譯叢》(讀者英稍微了解此學刊的創歷史及幾位創立者........)20年,領一份薪水做兩人份的工作20年 (可以與友人一日來回台北故宮看如窯展.......)
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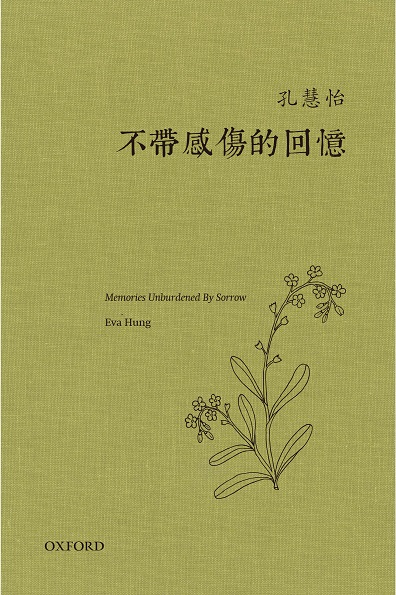
作者 孔慧怡 Eva Hung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7/11/
定價 HKD100
ISBN 9780190828189
目錄
新書試讀
書中記載的人和事,大多反映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現在回顧,那可以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本書所記的人物,有因為改朝換代而來到香港的,如楊宗翰、宋淇、鄺文美、蔡思果、王敬羲,他們被歷史的大潮推到這個小地方來,和香港結下幾十年的緣份,留下了文化印記。另有些不是香港人,但在他們生命裏,香港舉足輕重的,為此他們抱着特別的「香港情懷」:馬悅然、陳寧祖、高克毅和謝燁都是,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地理是他們生命的轉捩點;又比如華茲生和趙蘿蕤,晚年訪港,接觸到這個跟他們文化個性息息相關的地方,感受頗深。至於地道的香港人,像劉殿爵、黃兆傑、毛文福、也斯和張佩瑤,他們無一不以其終身事業說明香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建造出來的特殊文化。每章的焦點人物身邊還有動人的小故事,例如義助楊宗翰的清潔女工、劉殿爵的幫傭、徒弟和徒孫、與鄺文美相依幾十年的小妹姐等……是這樣的關係網編造了讓我們珍惜的香港。
------
後記
當時只道是尋常

我寫成這本書,可以說是無心插柳,也可以說是花了半輩子做準備功夫。
說無心插柳,因為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我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地早逝。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我繼續寫下去,這成了我回顧與老前輩們交往的誘因。心理學家認為在事業剛起步時遇到的人,對我們影響最大,在我來說的確是這樣。我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而在加入中文大學後,因為工作關係成了人生的「跳級生」,很自然地跟上一代的學者建立友誼;我的工作範圍多半牽涉國際學術界,這也反映在日常的生活圈子。跟那麼多閱歷深、識見廣的人交往三十餘年,一直覺得「理當如此」,現在事過境遷,才明白上天給了我多麼珍貴的機遇。

謝燁 顧城
人到中年,開始失去身邊的朋友,是大家都有的經驗;要是說我的情況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我最相熟的圈子裡,輩份比我高的人很多,所以我對「失去」的感受也來得早。每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世界,每個世界最重要的成份都是身邊熟悉的人;隨著他們的離逝,我們的世界是不是就變小了,甚至會有「七寳樓臺,拆下不成片段」的感嘆?

艾青
我算幸運,沒有太多消極的想法,每逢遇上可以跟已經去世的朋友分享的場景,就會覺得他們和我很靠近。在英語世界研究歷史的人回顧過往,不管講的是百多年前還是幾百年前的史實,往往愛用現在式敘事,恍惚古人舊事都在眼前,行內的說法是「歷史性的現在時態」historical present;中文沒有文法上的時態,但我回憶老朋友們,卻真有「現在時態」的感受——所謂歷歷如在眼前。
Wordsworth華茲華斯在“Surprised by Joy”一詩中責難自己因為意外的喜悅忘了傷逝的創痛,我覺得他很不通,也對不起已離世的人。相反,我願意有這樣的「意外喜悅」,更願意和別人分享,所以終於完成了這本書。

馬悅然
孔慧怡,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期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本書錯字似乎只一處,將《魔戒》打字成《魔介》。董橋先生的評語很可參考。
孔慧怡學貫中西,學術深厚,在宋淇、喬志高二位先生鼎力推薦下主持中文大學《譯叢》期刊多年,建樹超卓,譽滿遐邇,深得英美著名大學漢學圈子讚許。孔女士結交當代學人作家多年,友情既篤,赤誠相待,所著《不帶感傷的回憶》尤其珍稀,落筆清遠雋永,第一手資料化為第一流品題,十分難得。此書學術價值高超,文學品味脫俗,乃近年罕見之人物鈎沉之作,不宜忽視。
──董橋
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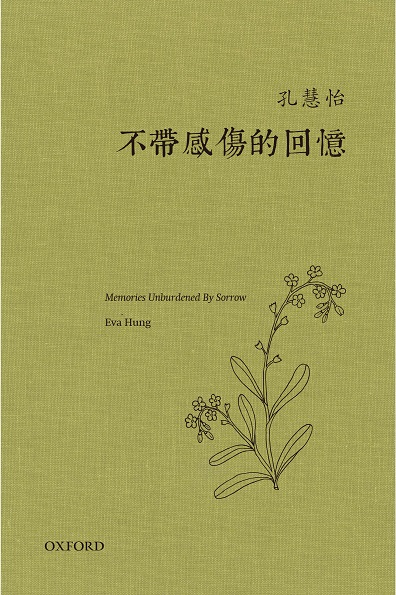
作者 孔慧怡 Eva Hung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7/11/
定價 HKD100
ISBN 9780190828189
目錄
新書試讀
書中記載的人和事,大多反映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現在回顧,那可以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本書所記的人物,有因為改朝換代而來到香港的,如楊宗翰、宋淇、鄺文美、蔡思果、王敬羲,他們被歷史的大潮推到這個小地方來,和香港結下幾十年的緣份,留下了文化印記。另有些不是香港人,但在他們生命裏,香港舉足輕重的,為此他們抱着特別的「香港情懷」:馬悅然、陳寧祖、高克毅和謝燁都是,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地理是他們生命的轉捩點;又比如華茲生和趙蘿蕤,晚年訪港,接觸到這個跟他們文化個性息息相關的地方,感受頗深。至於地道的香港人,像劉殿爵、黃兆傑、毛文福、也斯和張佩瑤,他們無一不以其終身事業說明香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建造出來的特殊文化。每章的焦點人物身邊還有動人的小故事,例如義助楊宗翰的清潔女工、劉殿爵的幫傭、徒弟和徒孫、與鄺文美相依幾十年的小妹姐等……是這樣的關係網編造了讓我們珍惜的香港。
------
孔慧怡| 不帶感傷的回憶 - Toments 找話題
toments.com/395501/
當時只道是尋常

我寫成這本書,可以說是無心插柳,也可以說是花了半輩子做準備功夫。
說無心插柳,因為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我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地早逝。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我繼續寫下去,這成了我回顧與老前輩們交往的誘因。心理學家認為在事業剛起步時遇到的人,對我們影響最大,在我來說的確是這樣。我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而在加入中文大學後,因為工作關係成了人生的「跳級生」,很自然地跟上一代的學者建立友誼;我的工作範圍多半牽涉國際學術界,這也反映在日常的生活圈子。跟那麼多閱歷深、識見廣的人交往三十餘年,一直覺得「理當如此」,現在事過境遷,才明白上天給了我多麼珍貴的機遇。

謝燁 顧城
人到中年,開始失去身邊的朋友,是大家都有的經驗;要是說我的情況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我最相熟的圈子裡,輩份比我高的人很多,所以我對「失去」的感受也來得早。每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世界,每個世界最重要的成份都是身邊熟悉的人;隨著他們的離逝,我們的世界是不是就變小了,甚至會有「七寳樓臺,拆下不成片段」的感嘆?

艾青
我算幸運,沒有太多消極的想法,每逢遇上可以跟已經去世的朋友分享的場景,就會覺得他們和我很靠近。在英語世界研究歷史的人回顧過往,不管講的是百多年前還是幾百年前的史實,往往愛用現在式敘事,恍惚古人舊事都在眼前,行內的說法是「歷史性的現在時態」historical present;中文沒有文法上的時態,但我回憶老朋友們,卻真有「現在時態」的感受——所謂歷歷如在眼前。
Wordsworth華茲華斯在“Surprised by Joy”一詩中責難自己因為意外的喜悅忘了傷逝的創痛,我覺得他很不通,也對不起已離世的人。相反,我願意有這樣的「意外喜悅」,更願意和別人分享,所以終於完成了這本書。

馬悅然
書中記載的人和事,大多反映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社會實況,現在回顧,那可以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不錯,那時香港比現在窮,生活條件比現在差,但吸收了大量從中國大陸湧進來的人才,不管文化、工商還是教育界,都因此「水漲船高」。舉個例說,當年《讀者文摘》在香港辦中文版,列位編輯的前輩不用說了,讓我最難忘的是每位校對都是中國著名大學科班出身,書法、印刻功夫了得,他們的文字技巧和嚴謹態度到今天已成絕唱,但他們讓後輩留下「雖未能至,而心嚮往之」的盼望,是這個社會的非物質遺產。

趙蘿蕤
我聽過很多關於上一代從大陸逃難到香港來的故事,覺得這一則最有代表性:一位朋友的父親和大學同窗當年從大陸逃到香港,第一要務是找工作,因為別無生計。剛好政府招聘警察,他們一起去報考,朋友的父親錄取了,那位高材生同窗卻落了空,原因是他的衣服少了一顆紐扣,他沒錢買新的填補上,只好拿從菜市場得來的鹹水草繫上,結果被指責「衣衫不整」,不配加入紀律部隊。二、三十年後,兩人話舊「憶當年」,那位同窗最感謝的是鹹水草:他做不成警察,加入工業界,成為香港六十年代冒起的大實業家;可是他沒提到的是他艱苦奮鬥的年頭。我常猜測他有多少次想到,要是當初有錢補好了衣服,他會跟同學一樣有鐵飯碗和養老金呢?人生際遇經常比編故事更曲折離奇,香港是個擠滿了人才的地方,像這樣的故事實在說不完。

鄺文美
這本書裡有不少因為改朝換代而跑到香港的人物,包括楊宗翰、宋淇、鄺文美、蔡思果、王敬羲等;他們被歷史的大潮推到這個小地方來,和香港結下幾十年的緣份,在那個歷史時刻留下文化印記。書中另一些人物不是香港人,但在他們生命裡,香港是個關鍵的地方,為此他們抱著特別的「香港情懷」:馬悅然、陳寧祖、高克毅和謝燁都是例子,香港的政治、文化和地理特質推動了他們生命的轉捩點;又比如華茲生和趙蘿蕤,在晚年訪港,接觸到這個跟關係著他們文化個性的地方,感受頗深。至於這裡記載的地道香港人,像劉殿爵、黃兆傑、毛文福、也斯和張佩瑤,無一不以他們的終身事業說明香港在特殊的歷史時空建造出來的特殊文化。每章的焦點人物身邊都有動人的小故事,例如義助楊宗翰的清潔女工、劉殿爵的幫傭、徒弟和徒孫、與鄺文美相依幾十年的小妹姐等……是這樣的關係網編造了讓我們珍惜的香港。

宋淇
說這本書是無心插柳,但也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附錄「一個英國人的漢學路」:我的丈夫卜立德和香港結緣始於一九五○年代底,可以說有大半生的香港因緣,常常有人問他當初怎麼學起中文來。我覺得他跟香港和中國那種「半裡半外」的關係很有意思,而一般人對歐洲漢學界知道的也不多,因此花了不少時間,千方百計勸服他動筆。

喬志高
我十多歲時跟很多同學一樣,愛看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短篇小說,可是說到印象深刻,首推他在著名長篇《人性枷鎖》裡的一個比喻。書中主角Philip想了解人生的意義,比他年長的朋友Cronshaw對他說:「去過巴黎的Cluny博物館嗎?那兒的波斯地毯有最繽紛的色彩、最精巧悅目的設計……但除了這些,你還會看出別的。你問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去看那些地毯吧,有一天你會得到答案。」

卜立德
碰上「波斯地毯」這個比喻已經幾十年了,我參透答案了嗎?也許眼前這本書就是答案。假如讀者在這裡看到繽紛的色彩、精巧的設計,那是因為我曾認識那麼多活得精彩的人;而在他們每個人的生命裡,同樣有很多人以智慧和誠信為他們的世界新增色彩、留下美妙的圖案。
希望這本書的讀者和我一樣,通過書中人物,讓自己的地毯染上一點他們的璀璨光芒。
二○一七年七月於英國梭士巴利
*****
看孔慧怡《不帶感傷的回憶》,有張舊照片格外難忘,那照片有六個人,主角顯然是港大舍監馮以浤和校長Kenneth Robinson,二人雄霸相片中央,英姿勃勃在對談;最右側是著名小說家Iris Murdoch,由於欠缺主角光環,閉上眼也慘被攝入鏡頭。但照片見於書中回憶黃兆傑的一章,本來的男主角去了哪裏?細看圖片解說,才知道背景中一位側身跟洋人談話,只隱約看見鼻子輪廓的男人,就是黃兆傑。看得我哈哈大笑。

黃兆傑
讀這本書是賞心樂事,從開捲到終結一直引人入勝,作者把很多我熟悉的文化和翻譯巨匠親切地重現眼前。孔慧怡行文筆調輕快,人物刻畫入微,讓一群東西方的文化之星光芒盡顯。書中人物知識淵博,貢獻良多,實應立碑傳以傳世。作者得天獨厚,與一代文化俊傑交遊多年,兼又好文而強記,一枝彩筆捕捉人物神髓,巨細無遺。此時此刻,這是我最樂意看的書。
──詹德隆
*****
星期日文學‧關詩珮:從中英翻譯歷史到香港文學立身
2019/2/17
【
明報專訊】編按:三聯要求學者關詩珮刪卻新書中有關六四等敏感內容未果,此事後以書店和作者和平解約而告終,但風波已引起本地文壇對出版審查的新一輪憂慮。事有湊巧,關的新作《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內容正好涉及書籍出版的問題,估計作家本身也是始料不及。現時此書已交付台灣聯經出版,據悉將在本年六月面世,在新書到手前,不妨先來了解關詩珮其人及其研究領域。
早前,新加坡學者關詩珮擬出版論集《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及後三聯出版社以內容涉及六四事件及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而要求作者刪減相關內容,否則拒絕出版該書,這宗新聞令文化界擾攘了一陣子,然後又歸於岑寂。這不奇怪,我城對時聞素來敏感,然而生活急促,大家都無暇翻查涉事人物的生平資料。然而,如果我們對這位學者的研究背景多一分認識,了解關詩珮的學術生涯,或會更清楚其研究興趣的發展,對於我城及其文學前途的啟示。
從網上找到的資訊,我們知道這位學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二○○九年東京大學特任準教授,同年起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她教授文學批評與文化理論、現代中國文學、中國文學與性別研究,及翻譯課程。近來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小說理論、中日比較文學及十九世紀中國翻譯史;亦為香港亞洲皇家學會「翻譯與殖民管治:香港及海峽殖民地(1842-1889)」研究計劃主持人。簡而言之,她的研究興趣在於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語文翻譯。
翻譯文本是歷史見證
以翻譯作為學術志趣,聽來很沉悶,誰知這也是比較文學或世界文學的重大課題。哲學家班雅明說語言不斷變動,翻譯的語言也不斷在變,因此追求一種能夠負載「永恆」翻譯的純粹語言。通俗一點說,偉大的翻譯家從心底裏總會追求一種不會被時間淘汰的譯文,既能兼顧信達雅原則,又不會因為語言的遞變而顯得過時。經典的翻譯不會因光陰而磨滅其光輝,或作為歷史的見證,或豐富譯文所運用的語言及其觀念,關於後者,大家可以想像到的例子是玄奘翻譯的佛教典籍。
作為香港人,當我們談到翻譯作為歷史見證文本時,自然想到英使來華的外交文件、不平等條約及殖民地報刊等譯文,西方與中國甚少接觸,而香港開埠一事,不單關係到中國近現代史之大變局,亦關乎中國文化重建知識體系,意義自是非凡。關詩珮對這方面抱有濃厚的興趣。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自然無法割捨攸關我城過去被遺忘的一頁,這方面也關係到香港兩種語文的互動。她曾多次撰文討論英國漢學家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在訓練英國外交部學習中文及廣東話方面的貢獻,在〈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1843-1870)〉(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期),關詩珮運用英國外交部及殖民地部的檔案文件,剖析威妥瑪當年如何運用自己的漢學知識改革英國外交部的中文翻譯課程、編製教材、招聘譯員,並參與教學工作等。
貫穿殖民地史的漢學家和翻譯官
作為十九世紀的西方列強之一,英國發展漢學的步伐比其他歐洲大國緩慢,但由於戰爭和殖民地管治的需要,而湧現了一批精通漢學的英倫學人,他們有濃厚的漢學根底,其翻譯教育工作亦引導殖民地的中文知識生產,威妥瑪就是其中關鍵人物,然而因其謹慎的外交官性格,我們對他師承的背景所知甚少。關詩珮在論文〈威妥瑪漢字字母化的追求——論新發現威妥瑪謄抄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手稿〉(刊於《漢學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四期)中指出,威妥瑪是透過抄寫英國早期傳教士馬禮遜的《字彙》開始學習中文的。
關詩珮作為翻譯界學者,梳理威妥瑪這一英國漢學家暨翻譯界先驅時,自是充滿景仰,但她也在文中指出,威妥瑪和另一位德裔翻譯家郭實臘(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或譯郭士立)都心裏明白,翻譯攸關大英帝國在華的長遠利益。關詩珮筆下的英方翻譯人物,如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方翻譯費倫(Samuel T. Fearon,或譯飛即);從法庭傳譯搖身一變成為殖民地各方調停者、藉此牟取私利的雙面譯者高和爾(Daniel Richard Caldwell),在中國眼中不啻是殖民主義的幫兇和買辦,研究殖民地翻譯官的歷史似乎亦觸及到現今中國所不齒的歷史。
這一頁殖民地歷史中,不乏漢學家的身影,英國漢學家與他們的歐洲同行有着一個關鍵的差別: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訓練治理殖民地、應付工商實務,以及口譯方面的專才。作家劉紹銘於《蘋果日報》(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發表一篇名為〈國粹.軟刀子.雜說〉的專欄文章,討論關詩珮的著作〈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時,提到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批判」港督金文泰的文章〈略談香港〉,金文泰正是理雅各(James Legge)的「翻譯官學生計劃」中職位最顯赫的學員。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自是認為中國傳統是傳染病,對文化比中國低得多的元朝和清朝產生負面影響,但西方人擁有更高文明,倘若英國人比中國人更聰明,中國人的腐敗文化,不單不能同化後者,反倒被後者用來治理中國這腐敗民族。魯迅對港英政府提倡國粹的看法,基本上被中共官方承襲過來,可見對於「翻譯制度」的看法,也不單純是語文的問題,而涉及政治鬥爭。
關詩珮一直研究這個課題,直到前年,才將其學術成果,輯錄成《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一書出版。按書中內容,我們可以追溯香港教育的一些源頭,例如當初理雅各認為中國各地有自己的方言,而翻譯官學員所接觸的多為廣府方言,故取廣府話而捨北京官話作為官方中文的口頭語言,這與日後香港兩文三語的格局有關,並且逐漸奠定港人身分的要素,對港英中文翻譯制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必然涉及殖民地身分認同問題。
村上春樹譯本與翻譯的局限
關詩珮也關注華文世界的日語文學翻譯,她的〈知識生產的場域與村上春樹在香港的傳播〉,就梳理華文世界翻譯村上春樹小說的始末,包括博益版和英譯本的誤譯。博益出版葉蕙的譯本,是最早的村上小說譯本,但這個譯本也「簡化、錯譯和漏譯了不少細節」,然而關詩珮藉此討論的「原譯中心論」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在她看來,許多論者(如湯禎兆)抱持原文是神聖文本的想法,指摘博益版的譯文不忠實,歸咎譯者和出版社不盡責,卻忽略了我們對村上小說的認識都建基於博益版本的基礎上,而翻譯背後也有着不同時代的限制。本身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成立的博益出版社,並不是一間旨於傳播知識的出版機構,當時以袋裝書形式出版村上小說,純粹為了向經濟起飛所催生對知識多元化有所渴求的中產或白領,提供消遣讀物。
從村上小說的翻譯,我們可否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多一點的理解?我們總是認為創作文本是神聖而恆久不變的,但創作和翻譯一樣,也因應受時空局限的受眾,而呈現出獨特、多變的面貌,而我們這些受眾總是被當下的政治和社會現况影響。我們或許可以想像一下博益譯本對於香港文學的意義,又或者,如果村上譯本在數年後由台灣或中國大陸出版社包辦,對兩岸三地文學創作又會產生如何的意義?文中也輕輕提及到,日後港台讀者和中國大陸讀者,對於台灣時報出版的賴明珠譯本和中國譯文出版的林少華譯本,在網路上掀起了哪個版本更好的爭端,這又遠超了翻譯的問題,因為翻譯所處理的是語言,而語言既建立我們的認同感,又是政治的前提。
作為翻譯系學者,除英語翻譯外,關詩珮還熟諳日語文學及其引介。也許由於民族主義的原因,一直以來較少論者探討日語文學對香港文學的影響。若論源頭,則早於八十年代香港哈日潮以前即注意日本文學的兒童文學家何紫可算是始作俑者之一。關詩珮於二○一八年五月寫的論文〈「『漢』文『和』讀法」——何紫兒童文化事業中的日本記憶(70-90年代)〉可謂這方面的鈎沉成果。這位兒童文學家決定理性地了解日本,他大量閱讀有關日本的書籍後,深受日本平民在戰後重建家園的精神感染,然而他只看懂日文著作上的漢字,卻能抽取大意。關詩珮這篇文章從何紫的例子思考大部分香港人學習日語的方法,並認為這類似梁啟超於晚清時提倡的「和文漢讀法」。何紫和八十年代「哈日潮」下許多熱愛文化的香港人一樣,他們深受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質吸引,因而捨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成見。這也說明,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的香港(一如關詩珮一再強調的),在日本文化(其載體包括文學作品、動漫和流行電視劇在內)裏面找到了吸引他們,又同屬東亞文化的精神特質。
繞不開政治和歷史的香港文學
香港的歷史,從來都是中英甚至是中美雙方角力場的歷史,在文學方面,香港深受西方和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既源於華語文學的傳統,香港人大多以華語書寫,但與中國大陸或台灣文學又全然不同。另一方面,香港文學又深受中港時局影響,研究香港文學就繞不開政治話題,我們既批判從英國人角度美化殖民的論述,又厭惡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立場。《全球香港文學》還未出版,我們無法得知那些被視為敏感題材的確切內容是什麼,但不管香港或香港文學在中國官方的眼中是什麼,它總有着官方定義所忽略的面貌,那些受時代或歷史事情所激發的思考,往往就是官方所不願承認的書寫題材。
而關詩珮對香港文學的觀點,可見於她研究施叔青、董啟章、鍾曉陽等香港作家的文章裏,其中一篇較為著名的,是她早於二○○○年寫的科大碩士論文〈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關詩珮在論文中提出後現代史學家對「歷史」的新定義,即歷史從來就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人為的、主觀的書寫,而香港文學正是發揮這類作用的文本。論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和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及《地圖集》作為歷史書寫的例子:《香港三部曲》透過描述名為黃得雲的女子,背景由開埠至回歸,把香港視為一個主體;後者以後現代筆法一邊建構一邊拆解這個主體。生於台灣的施叔青以一種外來者的眼光來看香港,小說把主角黃得雲寫成供洋人發泄性慾的娼妓,任何香港讀者都很難會產生共鳴。施叔青是外來者,她只能透過歷史想像去書寫香港,相比之下,董啟章所書寫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成長經驗。
然而《香港三部曲》與〈永盛街興衰史〉都有一個共通的轉捩點,就是六四事件。對於不能認同香港的施叔青而言,透過見證六四事件在香港的迴響,施叔青認同了香港人的身分;而董啟章筆下的「我」則在六四事件後舉家移民,以至重新思考香港人的文化身分。發生多年以後,我們依然無法否認,「六四事件」是一次很弔詭的經驗,它以一種否定的方式迫使香港人詰問自身的命運,並從中思考「我」是/不是誰,我應該是/不是怎樣。這大概就是三聯逼令作者刪減的內容,然而「六四」不過是催化香港人思考自身身分、命運的導火線而已,要用自己的視角而捨中國官方意識來講述香港的故事,這恐怕也不見容於當權者。
文 \\ 彭伊仁
圖 \\ 關詩珮
編輯 \\ 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
星期日文學‧孔慧怡:譯家的回憶,文人的交往
2020/2/16

 共3幅
共3幅 
【明報專訊】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於去年尾揭曉,散文組雙年獎由孔慧怡奪得,得獎作《不帶感傷的回憶》記錄了作者與不同文化人交往的故事,她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後來加入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與上一代的學者建立深厚的友誼。
訪問地點約在大埔的綠匯學苑,由孔慧怡推介,她笑說:「我想讓多點人認識這個地方,所以常常約朋友在這裏碰頭。」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署,建築物保留了眾多特色,包括用作降溫的遊廊和百葉窗設計,採用筒瓦及片瓦、以本地建築方法興建的中式木屋頂結構等。我們在「慧食堂」餐廳坐下來,點了兩杯有機茶,開始聊天。
以文字傳遞人物個性
問到孔慧怡的得獎感受,她說非常驚訝,皆因當初寫成一本書,算是無心插柳。她引用了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話:「動筆寫作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麼,只能努力嘗試;到看出了潛能,願景就會隨着變大。但只要把願景訴諸文字,還是得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寫,一行又一行。」
她說,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她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早逝,後來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她寫下去,這就成了她回顧與那些老前輩交往的誘因。除了梅子,另一個要多謝的人,是出版社編輯林道群,二人在一次書展偶然相遇,他提議將她的文章結集成書。成書後,孔慧怡特別請來張曼儀為她寫序,張曼儀是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最熟悉的導師,也是她極為敬佩的人。張曼儀在代序上寫到:「這本書憶念當代十六位已逝去的文化人……這些人物都是一時俊彥,其中十位是殿堂級的翻譯家:從庚子賠款留美的前清旗人楊宗翰到本港翻譯界熟悉的喬志高、宋淇、劉殿爵,到美國的漢學家華茲生,到前幾年離世的張佩瑤,全是現當代翻譯史不能遺漏的角色。」
「我記得頭兩篇寫的是也斯和黃兆傑,一開始寫的篇幅較短,後來知道要長時間寫下去,我便想它的作用是什麼,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把人物的個性傳遞出來,於是在每一章也添加了不少內容。」以劉殿爵為例,在孔慧怡的筆下,其鬼馬調皮的個性躍然紙上。
D.C. Lau的幽默與頑皮
在〈劉殿爵:金雞獨立〉一章中,孔慧怡甫開首便把劉教授孩子氣的一面呈現出來:「一個初秋的傍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大門外站着兩個人,男的六十多歲,世界知名學者,女的剛三十出頭,學術界的初生之犢。兩人一起倒數:『三、二、一,開始』,每人提起一隻腳,比賽誰的金雞獨立能耐更強。」(頁一○一)
根據書中所述,但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念翻譯的學生,都會知道D. C. Lau的名字,因為他的英譯《孟子》和原文一起高高列在一年級學生的書單中。戴着「知名學者」這頂光環,不免會被人當作是不苟言笑的嚴肅書生,然而,透過孔慧怡的文字紀錄,我們得以窺探鼎鼎大名的D. C. Lau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很喜歡跟別人說學術界的趣聞,其中一宗是這樣的:
「英國的垃圾桶有四尺高,放在屋外,便於政府垃圾車收集。愛丁堡大學John Scott的太太身材嬌小,但說話比較囉嗦。有一天不知何事,他忽然覺得煩不過來,把太太抱起來,走到屋外,拉開垃圾桶蓋,雙手把太太舉起,放進桶裏,把蓋蓋上,說一句:『這才是你的地方。』自己跑回屋裏去。」(頁一二○)
除了和別人談笑風生外,劉殿爵不時會和作者討論文學,有一回他問她怎麼看晏幾道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最後兩句;這首詞是作者追憶他第一次和歌伎小蘋相見的情况)。她回答說:「是說當月亮很好,小蘋三更半夜才離開他家。」沒想到劉殿爵反問:「如果『明月』和『彩雲』都是人名呢?」這席話猶如當頭棒喝,令她想深了一層:「十多歲的歌伎獨來獨往,在當時的社會說得過去嗎?假如是明月、彩雲和小蘋三人應邀到晏家,筵席過後明月提着燈籠和彩雲一起離開,那就是說小蘋當晚沒有走。」(頁一一七)與劉殿爵相識一場,孔慧怡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做學問要博大精深,過日子要簡簡單單」的生活哲理。
用三個字改變她一生
十六人當中,影響作者最深的人,非黃兆傑莫屬。
那時候,孔慧怡念中六,還不知道有黃兆傑這個人的存在。那年,她們學校的戲劇表演選了一部名為《萬世師表》的中文戲,內容講一個中文老師在抗日戰爭中彰顯氣節的故事。學校要求這部戲要有個英文名字,然而,「萬世師表」四個字包含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和讀書人的理念,一眾老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出了一個臨時劇名:「An Ideal Teacher」,這三個字顯然難登大雅之堂,有人便建議找外援,把難題送到港大中文系的翻譯專家那兒。(頁一八八)
這道難題最後落到黃兆傑博士的手中,他將「萬世師表」妙譯成「An Undefiled Heritage」,令孔慧怡驚喜萬分,把它比喻成一道「文化魔法」。馮睎乾後來發現,這道神來之筆可能內有乾坤:黃兆傑出身男拔萃,「An Undefiled Heritage」則是來自校歌的一句歌詞。不論如何,少女時代的孔慧怡,就這樣得知大學有一門叫「翻譯」的學科,後來她考入翻譯系,走上翻譯研究的路,短短三個英文字影響了她的一生,難怪她形容黃兆傑是一隻輕拍翅膀的蝴蝶,把她推往事業的起點。(頁一九一)
提起黃兆傑,孔慧怡帶點惋惜地說:「他從不知道這個小故事,我第一次提起,是他彌留之際。我和他一個後來成了我同事的學生,一起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已經昏迷了,同場還有兩個他比較後期的學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他,我才說起這件事。」
學習翻譯的法則
孔慧怡是一個很喜歡學習法則的人,她說:「所有遊戲的玩法,我都願意去學,但之後我便會很快失去興趣,因為我對輸贏沒太大感覺。當年劉教授說要教我捉圍棋,我常在一旁看他和其他人捉棋,卻覺得這個遊戲沒有樂趣。」翻譯這一門學科,雖然有很多規則,偏偏能令她樂此不疲。
念了翻譯科後,孔慧怡發現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比較好玩,她說:
「很多東西不能直接對譯,例如顏色。在中國文化中,紅色象徵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卻是代表危險。但是,我們要留意文化也會隨着時代而改變,像很多唐朝的鬼古中,裏面的美女是穿着青衣來結婚的,因此紅色也並非向來都是屬於喜慶的顏色。此外,古人眼中的黃色,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啡色,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啡色這個字來表達。」她又補充:「香港是一個雙語城市,一說翻譯容易令人直接聯想到中英對譯,但其實早期香港與國內開會也需要即時傳譯,就是廣東話與普通話。」
孔慧怡出道不久就進駐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以她三十出頭之齡來說可謂非同凡響。書中提到,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她戰戰兢兢地踏入宋家,與中心的前主管宋淇見面。在作者眼中,宋淇是個厲害的人物,他在創校校長李卓敏時代影響力甚大,因為他的職位不在一般編制中,只需直接向校長負責。見面時,宋淇問了她一句:「你覺得Jane Austen怎麼樣?」孔慧怡回答:「她倒真的可以用『愛』字來形容:我十五歲看完了她所有作品。」宋先生聽罷眼睛一亮說:「我是如假包換的『珍迷』,怎麼你比我還早看完她的書!」一開始緊張不安的氣氛頓時煙消雲散,二人如覓知音般,講了一個鐘頭Jane Austen。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看到裏面記錄了許多對話,便以為我的記性很好。其實不是的。我以前常常嘗試寫日記,每次寫了兩天就停,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對話,其實都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情緒,如開心、感動、驚訝、憤怒等,這些感覺和場景我必定記得,我的腦袋就像一部照相機,將一個個畫面定格。」
寫過投訴信給校長
談到在中大的二十年工作生涯,孔慧怡說一開始就像打仗一般。「我的職位有點麻煩,身兼多職,除了要教書,又是研究中心的主管,更是《譯叢》的主編,當時《譯叢》嚴重脫期,加上在翻譯系教書又遇到不少行政、學生問題。」說到這裏,她哭笑不得地說:「學生的問題很有趣,我試過連續兩三年都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上不到你九時半的課,因為我住得遠,坐車會遲到啊。我聽完呆了,當年我住大埔,還不是準時上在香港大學八時半的課!」
第一年做三份工,孔慧怡忙到透不過氣,試過寫一首英文詩作投訴信給校長高錕,其中一句的意思是「我現在的時薪只比菲律賓傭人好一點點而已」(On an hourly basis I am paid/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a Filipina maid)。校長看了那首詩,孔慧怡才開始「甩難」,學校減輕了她教學上的職務,她也為自己定下目標,在十年內完成已經開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推動國際交流,然後在五十歲生日以前遞交辭職信。
孔慧怡說到做到,遞了辭職信以後,自二○○七年起,她便隨丈夫移居英國,兩人於小鎮梳士巴利(Salisbury)買了一間房子,過着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們都對香港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兩邊走,每逢冬天就會回香港探望親友。談到退休生活,她說:「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做牛做馬了二十年,很想純粹地去旅行,體驗一下作為一個遊人看到的風景,而不是我做學者時,被人指派我去看特定的景點。」頭幾年,她和丈夫去了歐洲不同地方旅遊,又閱讀了大量偵探書、歷史書,後來覺得悶了,二人又分別寫書。
不帶感傷的回憶
《不帶感傷的回憶》這個書名,意味着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孔慧怡說:「這個世界有那麼多人,如果兩個人能夠相遇而且做到朋友,就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然而,她始終心存遺憾:「我覺得我跟每位朋友都見得不夠多,每次想起馬悅然過世,我都很後悔那時沒有飛過去見他一面,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能見到他了。近年我的母親身體變差,我每次來香港都要照顧母親,與朋友碰頭的機會也少了。」
詩人北島曾說:「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慶幸孔慧怡以文字如照相機般,近距離為昔日的文壇明星以及他們的時代,拍下一張張大特寫。目前,她已開展了另一個寫作計劃,寫大埔社區的歷史,期望在二○二一年完成著作,出版一本屬於香港的故事。
info:孔慧怡
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其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著有《不帶感傷的回憶》、《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遨遊江海:郵輪、河輪文化之旅》等。
文//柯美君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明報專訊】編按:三聯要求學者關詩珮刪卻新書中有關六四等敏感內容未果,此事後以書店和作者和平解約而告終,但風波已引起本地文壇對出版審查的新一輪憂慮。事有湊巧,關的新作《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內容正好涉及書籍出版的問題,估計作家本身也是始料不及。現時此書已交付台灣聯經出版,據悉將在本年六月面世,在新書到手前,不妨先來了解關詩珮其人及其研究領域。
早前,新加坡學者關詩珮擬出版論集《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及後三聯出版社以內容涉及六四事件及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而要求作者刪減相關內容,否則拒絕出版該書,這宗新聞令文化界擾攘了一陣子,然後又歸於岑寂。這不奇怪,我城對時聞素來敏感,然而生活急促,大家都無暇翻查涉事人物的生平資料。然而,如果我們對這位學者的研究背景多一分認識,了解關詩珮的學術生涯,或會更清楚其研究興趣的發展,對於我城及其文學前途的啟示。
從網上找到的資訊,我們知道這位學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二○○九年東京大學特任準教授,同年起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她教授文學批評與文化理論、現代中國文學、中國文學與性別研究,及翻譯課程。近來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小說理論、中日比較文學及十九世紀中國翻譯史;亦為香港亞洲皇家學會「翻譯與殖民管治:香港及海峽殖民地(1842-1889)」研究計劃主持人。簡而言之,她的研究興趣在於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語文翻譯。
翻譯文本是歷史見證
以翻譯作為學術志趣,聽來很沉悶,誰知這也是比較文學或世界文學的重大課題。哲學家班雅明說語言不斷變動,翻譯的語言也不斷在變,因此追求一種能夠負載「永恆」翻譯的純粹語言。通俗一點說,偉大的翻譯家從心底裏總會追求一種不會被時間淘汰的譯文,既能兼顧信達雅原則,又不會因為語言的遞變而顯得過時。經典的翻譯不會因光陰而磨滅其光輝,或作為歷史的見證,或豐富譯文所運用的語言及其觀念,關於後者,大家可以想像到的例子是玄奘翻譯的佛教典籍。
作為香港人,當我們談到翻譯作為歷史見證文本時,自然想到英使來華的外交文件、不平等條約及殖民地報刊等譯文,西方與中國甚少接觸,而香港開埠一事,不單關係到中國近現代史之大變局,亦關乎中國文化重建知識體系,意義自是非凡。關詩珮對這方面抱有濃厚的興趣。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自然無法割捨攸關我城過去被遺忘的一頁,這方面也關係到香港兩種語文的互動。她曾多次撰文討論英國漢學家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在訓練英國外交部學習中文及廣東話方面的貢獻,在〈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劃(1843-1870)〉(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期),關詩珮運用英國外交部及殖民地部的檔案文件,剖析威妥瑪當年如何運用自己的漢學知識改革英國外交部的中文翻譯課程、編製教材、招聘譯員,並參與教學工作等。
貫穿殖民地史的漢學家和翻譯官
作為十九世紀的西方列強之一,英國發展漢學的步伐比其他歐洲大國緩慢,但由於戰爭和殖民地管治的需要,而湧現了一批精通漢學的英倫學人,他們有濃厚的漢學根底,其翻譯教育工作亦引導殖民地的中文知識生產,威妥瑪就是其中關鍵人物,然而因其謹慎的外交官性格,我們對他師承的背景所知甚少。關詩珮在論文〈威妥瑪漢字字母化的追求——論新發現威妥瑪謄抄馬禮遜《廣東省土話字彙》及裨治文《廣東方言彙編》手稿〉(刊於《漢學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四期)中指出,威妥瑪是透過抄寫英國早期傳教士馬禮遜的《字彙》開始學習中文的。
關詩珮作為翻譯界學者,梳理威妥瑪這一英國漢學家暨翻譯界先驅時,自是充滿景仰,但她也在文中指出,威妥瑪和另一位德裔翻譯家郭實臘(C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或譯郭士立)都心裏明白,翻譯攸關大英帝國在華的長遠利益。關詩珮筆下的英方翻譯人物,如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方翻譯費倫(Samuel T. Fearon,或譯飛即);從法庭傳譯搖身一變成為殖民地各方調停者、藉此牟取私利的雙面譯者高和爾(Daniel Richard Caldwell),在中國眼中不啻是殖民主義的幫兇和買辦,研究殖民地翻譯官的歷史似乎亦觸及到現今中國所不齒的歷史。
這一頁殖民地歷史中,不乏漢學家的身影,英國漢學家與他們的歐洲同行有着一個關鍵的差別: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訓練治理殖民地、應付工商實務,以及口譯方面的專才。作家劉紹銘於《蘋果日報》(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發表一篇名為〈國粹.軟刀子.雜說〉的專欄文章,討論關詩珮的著作〈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時,提到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批判」港督金文泰的文章〈略談香港〉,金文泰正是理雅各(James Legge)的「翻譯官學生計劃」中職位最顯赫的學員。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自是認為中國傳統是傳染病,對文化比中國低得多的元朝和清朝產生負面影響,但西方人擁有更高文明,倘若英國人比中國人更聰明,中國人的腐敗文化,不單不能同化後者,反倒被後者用來治理中國這腐敗民族。魯迅對港英政府提倡國粹的看法,基本上被中共官方承襲過來,可見對於「翻譯制度」的看法,也不單純是語文的問題,而涉及政治鬥爭。
關詩珮一直研究這個課題,直到前年,才將其學術成果,輯錄成《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一書出版。按書中內容,我們可以追溯香港教育的一些源頭,例如當初理雅各認為中國各地有自己的方言,而翻譯官學員所接觸的多為廣府方言,故取廣府話而捨北京官話作為官方中文的口頭語言,這與日後香港兩文三語的格局有關,並且逐漸奠定港人身分的要素,對港英中文翻譯制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必然涉及殖民地身分認同問題。
村上春樹譯本與翻譯的局限
關詩珮也關注華文世界的日語文學翻譯,她的〈知識生產的場域與村上春樹在香港的傳播〉,就梳理華文世界翻譯村上春樹小說的始末,包括博益版和英譯本的誤譯。博益出版葉蕙的譯本,是最早的村上小說譯本,但這個譯本也「簡化、錯譯和漏譯了不少細節」,然而關詩珮藉此討論的「原譯中心論」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在她看來,許多論者(如湯禎兆)抱持原文是神聖文本的想法,指摘博益版的譯文不忠實,歸咎譯者和出版社不盡責,卻忽略了我們對村上小說的認識都建基於博益版本的基礎上,而翻譯背後也有着不同時代的限制。本身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成立的博益出版社,並不是一間旨於傳播知識的出版機構,當時以袋裝書形式出版村上小說,純粹為了向經濟起飛所催生對知識多元化有所渴求的中產或白領,提供消遣讀物。
從村上小說的翻譯,我們可否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多一點的理解?我們總是認為創作文本是神聖而恆久不變的,但創作和翻譯一樣,也因應受時空局限的受眾,而呈現出獨特、多變的面貌,而我們這些受眾總是被當下的政治和社會現况影響。我們或許可以想像一下博益譯本對於香港文學的意義,又或者,如果村上譯本在數年後由台灣或中國大陸出版社包辦,對兩岸三地文學創作又會產生如何的意義?文中也輕輕提及到,日後港台讀者和中國大陸讀者,對於台灣時報出版的賴明珠譯本和中國譯文出版的林少華譯本,在網路上掀起了哪個版本更好的爭端,這又遠超了翻譯的問題,因為翻譯所處理的是語言,而語言既建立我們的認同感,又是政治的前提。
作為翻譯系學者,除英語翻譯外,關詩珮還熟諳日語文學及其引介。也許由於民族主義的原因,一直以來較少論者探討日語文學對香港文學的影響。若論源頭,則早於八十年代香港哈日潮以前即注意日本文學的兒童文學家何紫可算是始作俑者之一。關詩珮於二○一八年五月寫的論文〈「『漢』文『和』讀法」——何紫兒童文化事業中的日本記憶(70-90年代)〉可謂這方面的鈎沉成果。這位兒童文學家決定理性地了解日本,他大量閱讀有關日本的書籍後,深受日本平民在戰後重建家園的精神感染,然而他只看懂日文著作上的漢字,卻能抽取大意。關詩珮這篇文章從何紫的例子思考大部分香港人學習日語的方法,並認為這類似梁啟超於晚清時提倡的「和文漢讀法」。何紫和八十年代「哈日潮」下許多熱愛文化的香港人一樣,他們深受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質吸引,因而捨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成見。這也說明,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的香港(一如關詩珮一再強調的),在日本文化(其載體包括文學作品、動漫和流行電視劇在內)裏面找到了吸引他們,又同屬東亞文化的精神特質。
繞不開政治和歷史的香港文學
香港的歷史,從來都是中英甚至是中美雙方角力場的歷史,在文學方面,香港深受西方和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既源於華語文學的傳統,香港人大多以華語書寫,但與中國大陸或台灣文學又全然不同。另一方面,香港文學又深受中港時局影響,研究香港文學就繞不開政治話題,我們既批判從英國人角度美化殖民的論述,又厭惡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立場。《全球香港文學》還未出版,我們無法得知那些被視為敏感題材的確切內容是什麼,但不管香港或香港文學在中國官方的眼中是什麼,它總有着官方定義所忽略的面貌,那些受時代或歷史事情所激發的思考,往往就是官方所不願承認的書寫題材。
而關詩珮對香港文學的觀點,可見於她研究施叔青、董啟章、鍾曉陽等香港作家的文章裏,其中一篇較為著名的,是她早於二○○○年寫的科大碩士論文〈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關詩珮在論文中提出後現代史學家對「歷史」的新定義,即歷史從來就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人為的、主觀的書寫,而香港文學正是發揮這類作用的文本。論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和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及《地圖集》作為歷史書寫的例子:《香港三部曲》透過描述名為黃得雲的女子,背景由開埠至回歸,把香港視為一個主體;後者以後現代筆法一邊建構一邊拆解這個主體。生於台灣的施叔青以一種外來者的眼光來看香港,小說把主角黃得雲寫成供洋人發泄性慾的娼妓,任何香港讀者都很難會產生共鳴。施叔青是外來者,她只能透過歷史想像去書寫香港,相比之下,董啟章所書寫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成長經驗。
然而《香港三部曲》與〈永盛街興衰史〉都有一個共通的轉捩點,就是六四事件。對於不能認同香港的施叔青而言,透過見證六四事件在香港的迴響,施叔青認同了香港人的身分;而董啟章筆下的「我」則在六四事件後舉家移民,以至重新思考香港人的文化身分。發生多年以後,我們依然無法否認,「六四事件」是一次很弔詭的經驗,它以一種否定的方式迫使香港人詰問自身的命運,並從中思考「我」是/不是誰,我應該是/不是怎樣。這大概就是三聯逼令作者刪減的內容,然而「六四」不過是催化香港人思考自身身分、命運的導火線而已,要用自己的視角而捨中國官方意識來講述香港的故事,這恐怕也不見容於當權者。
文 \\ 彭伊仁
圖 \\ 關詩珮
編輯 \\ 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
星期日文學‧孔慧怡:譯家的回憶,文人的交往
2020/2/16

 共3幅
共3幅 
【明報專訊】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於去年尾揭曉,散文組雙年獎由孔慧怡奪得,得獎作《不帶感傷的回憶》記錄了作者與不同文化人交往的故事,她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認識了一些文化和出版界的前輩,後來加入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與上一代的學者建立深厚的友誼。
訪問地點約在大埔的綠匯學苑,由孔慧怡推介,她笑說:「我想讓多點人認識這個地方,所以常常約朋友在這裏碰頭。」綠匯學苑的前身是舊大埔警署,建築物保留了眾多特色,包括用作降溫的遊廊和百葉窗設計,採用筒瓦及片瓦、以本地建築方法興建的中式木屋頂結構等。我們在「慧食堂」餐廳坐下來,點了兩杯有機茶,開始聊天。
以文字傳遞人物個性
問到孔慧怡的得獎感受,她說非常驚訝,皆因當初寫成一本書,算是無心插柳。她引用了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話:「動筆寫作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麼,只能努力嘗試;到看出了潛能,願景就會隨着變大。但只要把願景訴諸文字,還是得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寫,一行又一行。」
她說,本來只打算寫兩三篇,觸動她寫作的原因是幾個同輩的朋友意外早逝,後來稿子在《城市文藝》發表後,主編梅子不斷勸她寫下去,這就成了她回顧與那些老前輩交往的誘因。除了梅子,另一個要多謝的人,是出版社編輯林道群,二人在一次書展偶然相遇,他提議將她的文章結集成書。成書後,孔慧怡特別請來張曼儀為她寫序,張曼儀是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最熟悉的導師,也是她極為敬佩的人。張曼儀在代序上寫到:「這本書憶念當代十六位已逝去的文化人……這些人物都是一時俊彥,其中十位是殿堂級的翻譯家:從庚子賠款留美的前清旗人楊宗翰到本港翻譯界熟悉的喬志高、宋淇、劉殿爵,到美國的漢學家華茲生,到前幾年離世的張佩瑤,全是現當代翻譯史不能遺漏的角色。」
「我記得頭兩篇寫的是也斯和黃兆傑,一開始寫的篇幅較短,後來知道要長時間寫下去,我便想它的作用是什麼,既然有這個機會,我想把人物的個性傳遞出來,於是在每一章也添加了不少內容。」以劉殿爵為例,在孔慧怡的筆下,其鬼馬調皮的個性躍然紙上。
D.C. Lau的幽默與頑皮
在〈劉殿爵:金雞獨立〉一章中,孔慧怡甫開首便把劉教授孩子氣的一面呈現出來:「一個初秋的傍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大門外站着兩個人,男的六十多歲,世界知名學者,女的剛三十出頭,學術界的初生之犢。兩人一起倒數:『三、二、一,開始』,每人提起一隻腳,比賽誰的金雞獨立能耐更強。」(頁一○一)
根據書中所述,但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念翻譯的學生,都會知道D. C. Lau的名字,因為他的英譯《孟子》和原文一起高高列在一年級學生的書單中。戴着「知名學者」這頂光環,不免會被人當作是不苟言笑的嚴肅書生,然而,透過孔慧怡的文字紀錄,我們得以窺探鼎鼎大名的D. C. Lau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很喜歡跟別人說學術界的趣聞,其中一宗是這樣的:
「英國的垃圾桶有四尺高,放在屋外,便於政府垃圾車收集。愛丁堡大學John Scott的太太身材嬌小,但說話比較囉嗦。有一天不知何事,他忽然覺得煩不過來,把太太抱起來,走到屋外,拉開垃圾桶蓋,雙手把太太舉起,放進桶裏,把蓋蓋上,說一句:『這才是你的地方。』自己跑回屋裏去。」(頁一二○)
除了和別人談笑風生外,劉殿爵不時會和作者討論文學,有一回他問她怎麼看晏幾道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最後兩句;這首詞是作者追憶他第一次和歌伎小蘋相見的情况)。她回答說:「是說當月亮很好,小蘋三更半夜才離開他家。」沒想到劉殿爵反問:「如果『明月』和『彩雲』都是人名呢?」這席話猶如當頭棒喝,令她想深了一層:「十多歲的歌伎獨來獨往,在當時的社會說得過去嗎?假如是明月、彩雲和小蘋三人應邀到晏家,筵席過後明月提着燈籠和彩雲一起離開,那就是說小蘋當晚沒有走。」(頁一一七)與劉殿爵相識一場,孔慧怡從他身上深深地體會到「做學問要博大精深,過日子要簡簡單單」的生活哲理。
用三個字改變她一生
十六人當中,影響作者最深的人,非黃兆傑莫屬。
那時候,孔慧怡念中六,還不知道有黃兆傑這個人的存在。那年,她們學校的戲劇表演選了一部名為《萬世師表》的中文戲,內容講一個中文老師在抗日戰爭中彰顯氣節的故事。學校要求這部戲要有個英文名字,然而,「萬世師表」四個字包含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和讀書人的理念,一眾老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出了一個臨時劇名:「An Ideal Teacher」,這三個字顯然難登大雅之堂,有人便建議找外援,把難題送到港大中文系的翻譯專家那兒。(頁一八八)
這道難題最後落到黃兆傑博士的手中,他將「萬世師表」妙譯成「An Undefiled Heritage」,令孔慧怡驚喜萬分,把它比喻成一道「文化魔法」。馮睎乾後來發現,這道神來之筆可能內有乾坤:黃兆傑出身男拔萃,「An Undefiled Heritage」則是來自校歌的一句歌詞。不論如何,少女時代的孔慧怡,就這樣得知大學有一門叫「翻譯」的學科,後來她考入翻譯系,走上翻譯研究的路,短短三個英文字影響了她的一生,難怪她形容黃兆傑是一隻輕拍翅膀的蝴蝶,把她推往事業的起點。(頁一九一)
提起黃兆傑,孔慧怡帶點惋惜地說:「他從不知道這個小故事,我第一次提起,是他彌留之際。我和他一個後來成了我同事的學生,一起去醫院探望他,那時他已經昏迷了,同場還有兩個他比較後期的學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他,我才說起這件事。」
學習翻譯的法則
孔慧怡是一個很喜歡學習法則的人,她說:「所有遊戲的玩法,我都願意去學,但之後我便會很快失去興趣,因為我對輸贏沒太大感覺。當年劉教授說要教我捉圍棋,我常在一旁看他和其他人捉棋,卻覺得這個遊戲沒有樂趣。」翻譯這一門學科,雖然有很多規則,偏偏能令她樂此不疲。
念了翻譯科後,孔慧怡發現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比較好玩,她說:
「很多東西不能直接對譯,例如顏色。在中國文化中,紅色象徵吉祥,但在西方文化中,紅色卻是代表危險。但是,我們要留意文化也會隨着時代而改變,像很多唐朝的鬼古中,裏面的美女是穿着青衣來結婚的,因此紅色也並非向來都是屬於喜慶的顏色。此外,古人眼中的黃色,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啡色,因為當時他們沒有啡色這個字來表達。」她又補充:「香港是一個雙語城市,一說翻譯容易令人直接聯想到中英對譯,但其實早期香港與國內開會也需要即時傳譯,就是廣東話與普通話。」
孔慧怡出道不久就進駐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以她三十出頭之齡來說可謂非同凡響。書中提到,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她戰戰兢兢地踏入宋家,與中心的前主管宋淇見面。在作者眼中,宋淇是個厲害的人物,他在創校校長李卓敏時代影響力甚大,因為他的職位不在一般編制中,只需直接向校長負責。見面時,宋淇問了她一句:「你覺得Jane Austen怎麼樣?」孔慧怡回答:「她倒真的可以用『愛』字來形容:我十五歲看完了她所有作品。」宋先生聽罷眼睛一亮說:「我是如假包換的『珍迷』,怎麼你比我還早看完她的書!」一開始緊張不安的氣氛頓時煙消雲散,二人如覓知音般,講了一個鐘頭Jane Austen。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看到裏面記錄了許多對話,便以為我的記性很好。其實不是的。我以前常常嘗試寫日記,每次寫了兩天就停,我在文章中引用的對話,其實都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情緒,如開心、感動、驚訝、憤怒等,這些感覺和場景我必定記得,我的腦袋就像一部照相機,將一個個畫面定格。」
寫過投訴信給校長
談到在中大的二十年工作生涯,孔慧怡說一開始就像打仗一般。「我的職位有點麻煩,身兼多職,除了要教書,又是研究中心的主管,更是《譯叢》的主編,當時《譯叢》嚴重脫期,加上在翻譯系教書又遇到不少行政、學生問題。」說到這裏,她哭笑不得地說:「學生的問題很有趣,我試過連續兩三年都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上不到你九時半的課,因為我住得遠,坐車會遲到啊。我聽完呆了,當年我住大埔,還不是準時上在香港大學八時半的課!」
第一年做三份工,孔慧怡忙到透不過氣,試過寫一首英文詩作投訴信給校長高錕,其中一句的意思是「我現在的時薪只比菲律賓傭人好一點點而已」(On an hourly basis I am paid/ just a little better than a Filipina maid)。校長看了那首詩,孔慧怡才開始「甩難」,學校減輕了她教學上的職務,她也為自己定下目標,在十年內完成已經開展的中國翻譯史研究,推動國際交流,然後在五十歲生日以前遞交辭職信。
孔慧怡說到做到,遞了辭職信以後,自二○○七年起,她便隨丈夫移居英國,兩人於小鎮梳士巴利(Salisbury)買了一間房子,過着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們都對香港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未來的日子兩邊走,每逢冬天就會回香港探望親友。談到退休生活,她說:「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做牛做馬了二十年,很想純粹地去旅行,體驗一下作為一個遊人看到的風景,而不是我做學者時,被人指派我去看特定的景點。」頭幾年,她和丈夫去了歐洲不同地方旅遊,又閱讀了大量偵探書、歷史書,後來覺得悶了,二人又分別寫書。
不帶感傷的回憶
《不帶感傷的回憶》這個書名,意味着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孔慧怡說:「這個世界有那麼多人,如果兩個人能夠相遇而且做到朋友,就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然而,她始終心存遺憾:「我覺得我跟每位朋友都見得不夠多,每次想起馬悅然過世,我都很後悔那時沒有飛過去見他一面,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能見到他了。近年我的母親身體變差,我每次來香港都要照顧母親,與朋友碰頭的機會也少了。」
詩人北島曾說:「人在的時候,以為總有機會,其實人生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慶幸孔慧怡以文字如照相機般,近距離為昔日的文壇明星以及他們的時代,拍下一張張大特寫。目前,她已開展了另一個寫作計劃,寫大埔社區的歷史,期望在二○二一年完成著作,出版一本屬於香港的故事。
info:孔慧怡
香港出生,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出掌翻譯研究中心,兼任國際刊物《譯叢》主編,歷時二十年,其間推動國際學人研究亞洲翻譯傳統,又以史料先行的方針重寫兩千多年的中國翻譯史,同時亦以英譯中國文學見重於漢學界,並多年從事文藝創作。十年前離開學術界,尋找個人空間。著有《不帶感傷的回憶》、《五四婚姻:女方的故事》、《遨遊江海:郵輪、河輪文化之旅》等。
文//柯美君
編輯//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