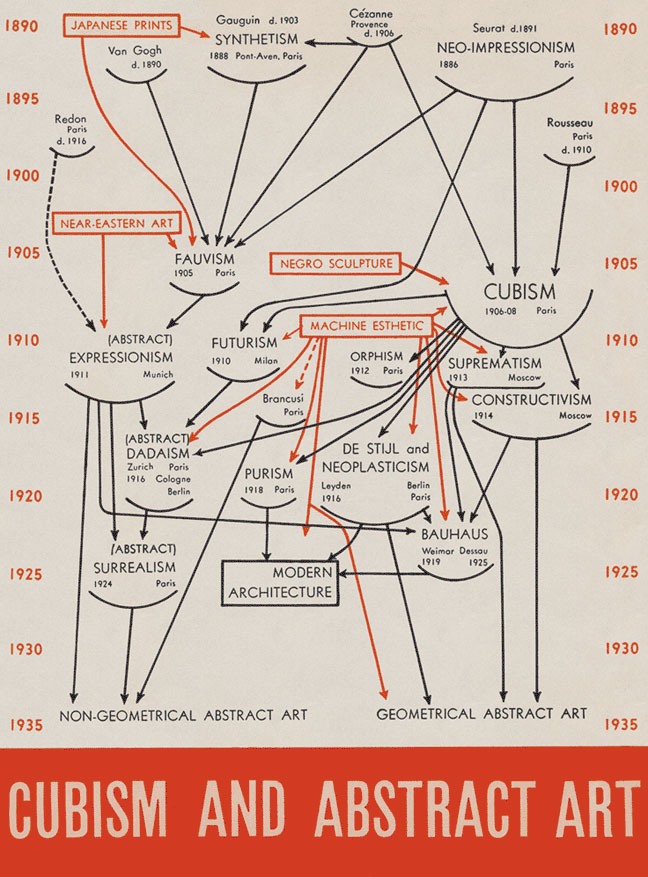他(彭淮棟先生)翻譯書,有時可達"會通"境界,譬如說,他覺得Said 的回憶錄《鄉關何處》(或譯《格格不入》)的某章,類似《魔山》的某一章。又譬如,Thomas Mann 書信(1945)的某句,出自歌德Goethe的:「打造藝術並無痛苦可言,但就像永遠在滾一塊總是必須重新往上推的的石頭。」 (參考 彭淮棟 《浮士德博士》(導讀和譯註本)頁63「 尼采小說」一節;比較Alber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1942) )
---
3. 很不幸的是,我的同學、好友 彭淮棟先生,除夕過世 (漢清講堂YouTube、譯藝blog等,都有其身影),所以我計畫找朋友來追思一下(其家屬不參加),希望有緣者來跟我講一聲:說你要參加 ,24日12點~13點。
2015年4月11
那年一些朋友在討論彭淮棟翻譯的Susan Sontag與友人去訪問Thomas Mann,
我卻是緊抓 Dr. Faustus中的小旋律,
Love's Labour's Lost
與彭淮棟就此通了5次email,第一封:
我認為第20-24章很有意思,也做一則翻譯筆記。
中國某網頁,只說彭淮棟的翻譯"典雅",如此而已:
彭淮棟,1953年生,新竹縣竹東鎮人,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肄業,曾任出版公司編輯,現任報紙編譯。譯有《後殖民理論》(Bart Moore-Gilbert)、《意義》(博藍尼)、《俄國思想家》(以撒亚·柏林)、《自由主義之後》(華勒斯坦)、《西方政治思想史》(麥克里蘭)、《鄉關何處》(薩依德)、《現實意識》(以撒亚·柏林)《智慧書─永恆的處世經典》(智庫出版)、《魔山》、《文化與社會》、《我兒子的故事》等書。
其實,彭淮棟 80年代中期的翻譯,由於追求"典雅",反而不夠清楚,應該可以重譯。譬如說, 彭淮棟譯 ,《喬治 艾略特》1985,牛津Past Masters系列,關於Middlemarch 的引文部分。
1977-78年,Essex大學圖書館的馬克思相關作品是一整書架,印象深。1978年 BBC 播影集"馬克思在倫敦"。2017.1 我介紹Walter Benjamin,他也不時會引用馬克思的作品,下文為一例:2017.2 我介紹 John Berger,印象中他引用馬克思的《一八四八哲學史稿》一段,我去查它的網路之中文和英文,都很不清楚,即翻譯的質量遠遜於Berger先生的英文。所以馬克思作品的中譯,可能還很有改善的空間。http://hctranslations.blogspot.tw/2017/02/blog-post_20.html
*****
雨水,送彭淮棟兄遠行
十九雨水,山邊微雨細細。年節的喜氣猶在,接到友人傳來訊息云,康樂過世逾十年,驚聞彭淮棟兄走了。更早以前,大年初一即收到友人傳訊云,彭淮棟兄除夕遠行,因逢過年,家屬低調,未通知親友。向鍾漢清學長求證,未獲確信。十九日接漢清學長來書云,二月廿四日將於漢清講堂舉辦彭淮棟追思會。復讀老友孫金君臉書貼文,終於確信我素所尊敬的阿棟哥已轉身遠行。
彭淮棟曾在翻譯瑣言中說,「你要翻譯,就必須很謙虛。譯路既長,可記之人之書之事蓋夥,唯區區素乏記性,加以老懶相尋,難追往者,何莫寧為吉人,權且忘其所忘,憶其所憶。此段感念,余至今時刻在心」。
2015年4月22日承蒙鍾漢清學長的盛情雅意,邀請我參加彭淮棟學長的譯者導讀,談托馬斯.曼(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裡的音樂。更早以前,2010年彭淮棟譯Edward W. Said《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出版社找我幫忙寫一篇導論。因翻譯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適巧又與音樂有關,鍾漢清學長請彭淮棟做一個譯者導讀的短講,邀我與會,乃得親聆阿棟哥討論音樂與文學。
認識彭淮棟學長三十年,倆人有著深厚的革命感情。1985年我乞食於編,任職《聯合文學》雜誌社,阿棟哥任職聯經出版公司,辦公室在忠孝東路基隆路口聯合報第三大樓,阿棟哥在七樓,我在六樓,因著是東海大學校友,時相過從。我編輯上每遇有歐美文學問題,常向阿棟哥請教,均能獲得完善的解答,心中時為感念。有幾期《聯合文學》刊載彭淮棟翻譯的「作家與作品」(Writers at Work)專欄,在翻譯過程中,為了查考已有之作者和書名,阿棟哥常比對台灣當時為數不多的歐美文學作品介紹或翻譯,意外發現某公之名作,內容多有抄龔,因而引發了一場小論戰。其後我因返校攻讀學位,轉任職《聯合報》新聞編輯,畢業乞食講堂,告別七年的編輯生涯。因為阿棟哥和我性格均屬溫暖而不熱情,故爾彼此間甚少相問。前次見面是2002年7月,我因腰傷到醫院做檢查與復健,阿棟哥帶小孩看感冒,倆人在醫院偶遇。
2015年4月22日鍾漢清學長邀我參加彭淮棟學長的譯者導讀,是與阿棟哥的最後聚談,那次聚會阿棟哥簽名送我《浮士德博士》,我則送他一支大長流毛筆,蓋因他喜用大長流臨李北海碑,適巧友人做了一批未加尼龍的大長流筆,因以相贈。不意三年後阿棟哥竟揮手自茲去,遠行無牽掛。
近年讀臺灣學者論文,常使用「語境」一詞,即英文之context,中國譯為語境;事實上臺灣有更適切的翻譯,即彭淮棟兄所譯的「脈絡」。每次讀到臺灣學者使用語境,就想到為什麼不用彭淮棟兄所譯的脈絡。另一個學術名詞「框架」(frame),倒是常為學術界所使用,最初似亦為彭淮棟兄所譯。
老友遠行,心中感念。雜記瑣事,以為送別。
彭教授,初二接到您的傳信,網路一查,報社公布其八百來篇文章,即知傳言屬實。後一日,與他妻女各一談--電話,心煩意亂,忘記跟您確信。
****
為《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寫的導讀: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12009297.html
在戰場撿拾破碎的彈片
這篇短文是為《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寫的導讀。譯者彭淮棟的譯筆出色當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依循薩依德的指引,穿越危崖深壑,採擷山谷裡的百合。

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作者:艾德華.薩依德
原文作者:Edward W. Said
譯者:彭淮棟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19日
坦白說,我並不確定知道薩依德的初意,是否要將這本《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寫成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雖然這本書的未完成,或許揭示了薩依德認為晚期風格的支離破碎、幽黯和不合時宜。麥可.伍德教授在整理這本書稿時,已盡其所能使書稿看起來齊整,但薩依德真正想表達的或許是支離破碎。我甚至懷疑薩依德打從一開始就不準備完成此書,而以此書為其晚期風格:一種反時代、支離破碎、幽黯、到處彌漫死亡氛圍的美學。或許我們可以從反整體、反圓融的角度切入這本書,並深入薩依德於書中所揭示的反社會、反和諧、反整體之基本概念,才能進入本書的核心,一種反完整的晚期風格。
在正式入進入討論之前,我先略述《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各章題旨,因為我的討論將不會依循大綱模式順序進行,而以個人的索引和解讀為主,故先將各章大要略加敘述,以免掛一漏萬。
第一章〈適時與遲晚〉,晚期風格的意涵,討論主要對象為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晚期作品;第二章〈返回十八世紀〉分析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的《玫瑰騎士》;第三章〈《女人皆如此》:衝擊極限〉以莫札特(W. Amadeus Mozart)歌劇《女人皆如此》為例,說明晚期風格與成熟之作的差別;第四章《論惹內》論析支持巴基斯坦建國與阿爾及利獨立運動的惹內(Jean Genet),如何在《愛的俘虜》與《屏風》中,呈現作者薩依德的西方/法國/基督教身分,如何與他者的文化搏鬥;第五章〈流連光景的舊秩序〉,以藍培杜沙(Tomasi di Lampedusa)的《豹》(The Leopard),以及維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將《豹》改編為電影《浩氣蓋山河》(Gattopardo Il)為討論對象;第六章〈炫技家/知識分子〉詮釋葛林.顧爾德(Glenn Gould)的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演奏;第七章〈晚期風格綜覽〉有類總結而非總結,討論各種可能的晚期風格。
在開始閱讀本書時,我其實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想從本書找尋所謂晚期風格的整體性。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想法根本是椽木求魚,因為薩依德要呈現的剛好是反整體性的支離破碎。找到這個切入點之後,我方始進入薩依德所討論的晚期風格之世界。
薩依德指出,所謂晚期風格、晚期意識或晚期特質,是「一種放逐的形式」。這種放逐包括與時代之扞格,殘缺的、片段,置連貫於不顧的性格。我的討論將依循兩條線索進行,一條是薩依德在《論晚期風格》中所賦予的;另一條是我對書中所討論課題的另加引申,提出個人的見解與薩依德對話。雖然這個對話是單向的,亦即我對薩依德論題的提問,而薩依德無法據此回應或論辨。
在閱讀這本《論晚期風格》,和撰寫這篇導論時,我不斷聆聽薩依德所提到的音樂作品,但我並不確定知道薩依德是否聽過我所聽的這些演奏;譬如薩依德提到貝多芬晚期作品的重要代表《莊嚴彌撒曲》(Missa Solemnis in D Major, Op.123)和《第廿九號鋼琴奏鳴曲:漢馬克拉維》(Hammerklavier);《漢馬克拉維》德文意為「琴槌」,是現存貝多芬最巨大的鋼琴奏鳴曲。我在這裡當然不可能窮舉所有重要的錄音演奏,僅以其中兩個對比明顯的演奏為例:一個是鋼琴獅王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在DECCA的錄音(Wilhelm Backhaus/ Beethoven/ The Complete Piano Sonatas/ DECCA SXLA 6452-61. c. 1970. 本文所列均為黑膠唱片(Vinyl Disk, LP)編號;我是刻意這麼做的,因為就薩依德對晚期風格的定義,與時代背反、支離破碎、不合時宜、彌漫死亡氛圍的美學,黑膠唱片在數位CD問世之後的命運差近乎是。早在1980年代後期,即有論者稱黑膠唱片是死亡的美學,雖然迄21世紀猶有嗜痴者,但與潮流所趨之CD,終究不可同日而語。有興趣蒐尋本文所列唱片的讀者,不難從指揮家、奏唱家,找到相同錄音的CD),這個錄音收錄於巴克豪斯第二次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全集錄音中,但事實上是將他的第一次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的單聲道錄音,放到立體聲錄音的全集唱片中魚目混珠。據專家考證,巴克豪斯第二次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全集時年歲已高,沒力氣彈完《漢馬克拉維》。雖然有論者指出,巴克豪斯單聲道錄音那次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更能呈顯其鋼琴獅王之美名,但畢竟是1950年代的單聲道錄音,與愛樂者所追求的立體聲錄音終究有別。巴克豪斯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繼承傳統的演奏方式,即左手彈和絃,右手為主旋律,這是古典樂派以後鋼琴奏鳴曲的主要結構形式。我在史納伯(Artur Schnabel)的唱片錄音,也聽到類似的傳統(Artur Schnabel/ Beethoven/ The complete Piano Sonatas/ Angel GRM 4005)。史納伯是第一位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的二十世紀鋼琴家,我發現/或至少在我的聆聽印象裡,巴克豪斯和史納伯是一脈相承的。
我要提的另一個演奏家是吉利爾斯(Emil Gilels),在所錄唱片中,吉利爾斯將《漢馬克拉維》用賦格曲的方式演奏(Emil Gilels/ Ludwig van Beethoven: Piano Sonata No. 29(op. 106) Hammerklavier/ DG 410 527-1, C.1983),彈成複音音樂的樣式,左右手演奏不同的旋律線,形成兩條主旋律的樣式。在我的聆聽經驗中,史納伯/巴克豪斯的演奏傳統,使《漢馬克拉維》呈現斷裂和支離破碎的不可解,一如貝多芬的晚期絃樂四重奏,音樂界名之曰「天書」。但在吉利爾斯的演奏中,我卻讀到兩條旋律線的分進合擊,結構雄偉,不斷向上仰望,宛若攀登生命的高峰。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吉利爾斯的最後錄音,貝多芬《第30、31號鋼琴奏鳴曲》(Emil Gilels/ Ludwig van Beethoven: Piano Sonata No. 30(op. 109), 31(op. 110)/ DG 419 174-1, C.1985),在這兩首鋼琴奏鳴曲演奏中,吉利爾斯以靈明清澈的琴音,淡然地處理貝多芬的晚期作品,而左右手獨立的旋律線,和其演奏《漢馬克拉維》同樣採取賦格曲的方式演奏。《第30、31號鋼琴奏鳴曲》是吉利爾斯的最後錄音,與吉利爾斯早年現場演奏充滿熱情與雄辯的風格,有上下床之別。套用薩依德的理論,或許可視之為吉利爾斯的晚期風格。
薩依德這本遺著中,我個人覺得比較大的遺憾是沒有讀到作者對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的進一步討論。在本書第一章《適時與遲晚》中,薩依德引述阿多諾的討論,認為貝多芬的最後五首鋼琴奏鳴曲、《第九號交響曲》(Symphony No. 9 in D Minor,Op.125 “Choral”)、《莊嚴彌撒曲》、最後六首絃樂四重奏、十七首鋼琴小品,構成貝多芬的晚期風格,與其同時代的社會秩序形成矛盾、疏離的關係。然而,如所周知,《第九號交響曲:合唱》幾乎可被視為歐洲的「國歌」,許多重要場合都演奏這首曲子,柏林圍牆倒塌時,演奏的就是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我們也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拜魯特音樂節經過六年的重建,重新開幕時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指揮演出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這場演出所錄製的唱片,也成為二十世紀的偉大唱片(Wilhelm Furtwangler/ Bayreuth Festival Orchestra/ Schwarzkopf/ Hopf/ Beethoven: Symphony No. 9 in D Minor,Op.125 “Choral”/ Angel GRB 4003),愛樂者幾乎人手一套。如果薩依德認為《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代表貝多芬的晚期風格,那麼,要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因為薩依德所謂晚期風格,明顯帶有與社會秩序形成矛盾、支離破碎、幽黯、反時代、死亡的蔭影等意義,而《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似乎並不具備這些特色,可惜我們看不到薩依德進一步的說明了。
在討論頭多芬的作品時,薩依德對《莊嚴彌撒曲》著墨較多。薩依德引述阿多諾的觀點,認為《莊嚴彌撒曲》之難解、復古,以及對彌撒曲所做的奇異主觀價值重估,阿多諾稱之為「異化的大作」。薩依德認為貝多芬的《莊嚴彌撒曲》是一個倒返運動,退回未表現、未界定之境。然而,當我們聆聽不同指揮家的演繹時,或許會發現不同演奏,帶給閱聽人的感受天差地別,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的指揮似乎呈現了《莊嚴彌撒曲》的原型(Otto Klemperer/ 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 Chorus/ Soderstrom/ Kmentt/ Beethoven: Missa Solemnis in D Major, Op.123/ EMI SAN 165-6 SLS 922/2),一種地獄般的氛圍;但如果我們聆聽約夫姆(Eugen Jochum)的演奏(Eugen Jochum/Concertgebouw Orchestra, Amsterdam/ Beethoven: Missa Solemnis in D Major, Op.123/ Philips 6799 001. p. 1971),將會發現宛若清風和煦的天堂;類似的演繹也出現在貝姆(Karl Böhm)棒下(Karl Böhm/ Wiener Philharmonia Orchestra / Beethoven: Missa Solemnis in D Major, Op.123/ DG 2707 080, c. 1975)。那麼,究竟克倫培勒的讀譜貼近貝多芬?或者約夫姆和貝姆更靠近作曲者原意?音樂是一種再創作的形式,一般人很難透過總譜聆聽音樂,特別是交響曲、彌撒曲或歌劇總譜,往往非未受專業訓練者所能勝任。那麼,作曲者的風格將如何呈現?我們聽到的是作曲者之原意?或指揮家、奏唱家的演繹?答案是如此的模糊。
相對於貝多芬的晚期風格,薩依德在討論莫札特的作品時,並非取樣其最後遺作《安魂曲》,而是歌劇《女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或譯《馴悍記》)。但我要特別申明,在女性意識覺醒的今日,無論譯為《女人皆如此》或《馴悍記》,都很可能會引發紛爭。如果記憶無誤,《女人皆如此》最早的中文譯名,應是愛樂前輩張繼高(吳心柳)所譯,今日已約定成俗,似亦毋須多言呶呶。
《女人皆如此》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劇情的荒謬透頂,另一個是音樂的優美旋律。薩依德指出,《女人皆如此》劇情的興奮、喧鬧,情節荒謬、瑣屑,在在說明《女人皆如此》的通俗劇性格,我個人認為或可名之曰「維也納歌仔戲」。我不確定薩依德是否看過台灣的河洛歌仔戲,如若看過,或許會對《女人皆如此》的劇情感到釋懷。無論《三笑姻緣》、《梁山伯與祝英台》、《七世夫妻》,都有類似《女人皆如此》的荒謬劇情,雖然並非全然相同,但亦差相彷彿。我想大部分觀眾走進音樂廳,想看的應非《女人皆如此》之荒謬劇情,而是那「美得驚人的音樂」(薩依德語)。而在此劇中,女人的善變和不忠,慾望與滿足的邏輯迴路,既入此迴路,即無所逃避,亦無提升可言。借用今日之電腦術語,即進入永恆迴圈。然而,當觀眾聆賞這類歌劇時,無論選擇哪一位指揮的唱片或現場演出,恐怕仍是浸淫於優美的音樂居多。在美麗的旋律包裝下,閱聽人大部分時候其實是耽溺於感官的享受,而遺忘了劇情的荒謬。在唱片目錄中最容易找到的《女人皆如此》唱片,應是貝姆指揮的兩次錄音(Karl Böhm/ Philharmonia Orchestra/ Schwarzkopf/ Ludwig/ Steffek/ Kraus/ Taddei/ Berry / W. Amadeus Mozart: Cosi Fan Tutte/ EMI SAN 103-6 SLS 901-4 [4LPs]; 這個版本是薩依德在《論晚期風格》中曾提到的;Karl Böhm/ Wiener Philharmonia Orchestra/ W. Amadeus Mozart: Cosi Fan Tutte/ DG 2740 118 [3LPs],無論哪一套,都可以滿足愛樂者的感官享受。
薩依德指出,記省和遺忘是《女人皆如此》的基本主題。就莫札特歌劇而言,薩依德認為《女人皆如此》是晚期作品,《費加洛婚禮》和《唐喬凡尼》只是成熟之作,確然有其高明卓見。惟同屬成熟之作的《魔笛》卻是童話式作品,如果說《女人皆如此》是成人通俗鬧劇,《魔笛》的童話風格顯然與其有別;薩依德認為,雖然使用類似《女人皆如此》的證明和考驗故事,但在道德層面,《魔笛》寫成了比較能為人所接受的版本。因為「忠實」在《女人皆如此》落空,而在《魔笛》得伸。
在討論《女人皆如此》時,薩依德提出貝多芬的《費黛麗奧》(Fidelio)與之對照,認為貝多芬此劇係針對《女人皆如此》所作的回應。因此,《費黛麗奧》與《女人皆如此》是完全背反的。薩依德認為《費黛麗奧》斥責《女人皆如此》所代表的「南方」味道,劇中角色均狡猾、自私、耽於逸樂、缺乏罪疚感。故而《費黛麗奧》認真、沈篤、深刻嚴肅的氣氛,乃是對《女人皆如此》的批判。但不幸的是,愛樂人顯然喜愛《女人皆如此》遠勝於《費黛麗奧》。我想,對一般愛樂者而言,聆賞《女人皆如此》的次數,肯定要比聆賞《費黛麗奧》的次數多得多。甚或聆賞過《女人皆如此》的愛樂者,應該也多於《費黛麗奧》。這裡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音樂/歌劇的聆賞,和道德、正義顯然無甚關連。做為貝多芬唯一完成的歌劇,《費黛麗奧》明顯不受愛樂人青睞。有趣的是,貝多芬雖然一輩子只完成這齣歌劇,卻先後寫過四首序曲,即〈蕾奧諾拉序曲〉一至三號(Leonore Overtures 1,2,3),第四首即《費黛麗奧.序曲》。比較可能的揣測是,貝多芬真的很想寫好這齣歌劇,雖然完成後似乎長久以來一直不受愛樂人垂青。幾位二十世紀的名指揮家大都指揮過《費黛麗奧》,而我個人偏好卡納帕斯布許(Hans Knappertsbusch)的指揮(Hans Knappertsbusch/ Bavarian State Opera Orchestra, Chorus/ Beethoven: Fidelio/ Westminster WMS 1003 (3LPs); 《費黛麗奧》(Fidelio)原名《蕾奧諾拉》(Leonore),是貝多芬生平唯一的歌劇創作,此劇前後經過多次修改,始為今日之樣貌。《蕾奧諾拉》1805年首演時受到冷落,迫使貝多芬重新修改,將原本的三幕縮減為兩幕,最後在1814年寫下較簡短卻強而有力的《費黛麗奧.序曲》,並將劇名改為《費黛麗奧》重新三度推出。有一個《蕾奧諾拉》原始版本唱片,有興趣的讀者或可嚐鮮:Herbert Blomstedt/ Staatspelle Dresden/ Beethoven: Leonore / EMI 2 C 167-028535, c. 1976),那規模宏偉的管弦樂,和如實境般的場景,使這齣具有道德訓誡意義的歌劇,多了幾分人世的可親。
當鏡頭轉向二十世紀,加拿大鋼琴家葛林.顧爾德(Glenn Gould)的巴哈演奏,儼然成為歐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對於這位在生涯高峰的1964年,毅然離開音樂舞台的鋼琴怪傑,薩依德在《論晚期風格》中語多贊美。顧爾德在離開演奏舞台之後,以廣播錄音延續其音樂生命。其一生行徑不僅被拍成電影,並且成為歐美文化研究學者興致盎然的論題。薩依德指出,顧爾德很早就強調,巴哈的鍵盤作品,並非為任何一種樂器而寫。今日的愛樂者,如果沒有聽過顧爾德彈奏的巴哈,那麼,講話可能要小聲一點,不論你喜不喜歡顧爾德的演奏樣式,至少你得聽過。薩依德認為顧爾德對復興巴哈音樂的貢獻,其成就可能不下於大提琴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和指揮家李希特(Karl Richer)。卡薩爾斯發現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手稿並演奏此曲,無疑是二十世紀巴哈音樂復興運動的重要里程碑。而李希特以古樂器詮釋巴哈樂曲和清唱劇,亦具有重要的時代意涵。雖然後來哈農庫特(Nikolaus Harnoncourt)的巴哈清唱劇全集錄音,規模更為龐大,但李希特顯然是哈農庫特的先行者。
薩依德形容顧爾德創造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晚期特質,其方法是離開現場演奏舞台,頑固地在他活力仍然強烈之時,將生前變成身後。顧爾德演奏的巴哈,帶著一種深刻的特異主觀風調,然而入耳清新,有一種說教式的堅持,對位法嚴厲,毫無繁瑣的虛飾。薩依德認為顧爾德創造了新意義的巴哈,且因其獨特樣式,入耳可辨。顧爾德宣稱現場演奏會已死,因而轉向錄音室的「二次錄音」,以確保其演奏之絕對完美。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顧爾德的每次錄音都是獨一無二,卻又透過多次錄音之剪輯,以形塑其特殊風格的巴哈演奏。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經過剪輯的完美錄音,是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演奏,還是舞台演奏的偶然出錯,更具有唯一性?薩依德此處之論點其實是有點弔詭的。
薩依德提出創意(Invention)這個字來詮釋巴哈音樂的精神,也用這個字形容顧爾德的巴哈演奏,我個人覺得是極妥切的。Invention除了「創意」之外,還有「再生」的意涵,顧爾德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詮釋、發揮創意、修正、重新思考,每一場演奏都針對速度、音質、節奏、色彩、音調、樂句、聲部導進、抑揚頓挫各方面,殫精竭智,重新創造。因此,顧爾德選擇錄音室做為他晚期風格的體現方式,不斷探索巴哈的創意。有趣的是,當顧爾德選擇和作曲家站在一起,而非與消費大眾同一陣線,卻意外攫獲了閱聽人的青睞。其孤意與執著,帶著個人主觀風調的演奏樣式,遠離舞台,擁抱錄音室之特立獨行,卻意外成為許多愛樂者追尋、蒐藏的目標,毋寧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但文化研究者對顧爾德的關注和興致盎然,並不表示所有的愛樂者都步武其後。我自己對顧爾德的巴哈詮釋,固心儀其創意,但亦非完全接受,巴哈的部分曲目,我個人可能更喜愛杜蕾克(Rosalyn Tureck)或尼可萊耶娃(Tatyana Nikolayeva)的詮釋。對我而言,杜蕾克和尼可萊耶娃的演奏,是一種更和諧的音樂世界。顧爾德乾淨的觸鍵,均衡的左右手,確然在巴哈的複音音樂演奏上占盡優勢,或許我們可借用薩依德的「炫技」來形容。但有時我會喜歡更優美的演奏樣式,從容的上升,愉悅的下降,就這方面而言,尼可萊耶娃的《平均律》(The Well-Tempered Clavier)和《賦格的藝術》(The Art of Fugue)( Tatyana Nikolayeva/ Johann Christian Bach: The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I BWV 846~869/ Victor/Melodiya VIC-5024~6 (3LPs), Recorded in Oct. 1972, Melodia Studio, Moscow; Tatyana Nikolayeva/ Johann Christian Bach: The Art of Fugue, BWV 1080/ Victor/Melodiya VIC-5027~8 (2LPs), Recorded in 1967 Melodiya Studio, Moscow),是我比較常選擇聆聽的唱片。當然,在想到《郭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時,我必須承認自己常放在唱盤上的,仍然是顧爾德演奏錄音,包括速度飛快的1955年版(Glenn Gould/ Johann Christian Bach: Goldberg Variations/ CBS MS 7096 c.1955),和代表顧爾德晚期風格的1981年錄音(Glenn Gould/ Johann Christian Bach: Goldberg Variations/ CBS IM 37779, c. 1982)。1955年發行巴哈《郭德堡變奏曲》之後,顧爾德一炮而紅,從此歐美各地邀約不斷。1981年錄音的《郭德堡變奏曲》則是其絕命詩;因為錄完音後,顧爾德於1982年10月4日即在多倫多蒙主寵召。始於《郭德堡變奏曲》,終於《郭德堡變奏曲》,豈非正如薩依德所說的「既入此迴路,即無所逃避」,進入生命的永恆迴圈。
當場景回到二十世紀初,我們隨著薩依德的指引,將焦點放到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身上。薩依德從阿多諾的樂論切入,批評史特勞斯是耽於操縱的自大狂,模仿和杜撰而空無情感,無恥露才揚己,懷舊誇大。薩依德在此表述,作曲家的晚期風格並非出現於其最後作品,而是某些與時代齣齬、疏離之作。就史特勞斯而言,代表其圓熟進步之作的是《莎樂美》(Salome)和《伊蕾克特拉》(Elektra)。《伊蕾克特拉》於1909年問世,與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的表現主義單幕劇《期待》(Erwartung)同年;但1911年完成的《玫瑰騎士》,卻退回甜膩、走回頭路的世界,一個講調性、思想溫馴的世界。與同時代的作曲家如亨特密特(Paul Hindemith)、史特拉汶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巴爾托克(Bela Bartok)、布列頓(Lord Benjamin Britten)等人相較,史特勞斯顯然退回到舊秩序裡。薩依德的意思是,史特勞斯在音樂上的發展非常少,反而退回到調性音樂的秩序中,有別於其早年發展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的半音主義、甚至發展到超越《崔士坦與易索德》(Tristan und Isolde)的境地。薩依德指出,史特勞斯非僅《玫瑰騎士》回到十八世紀那個逝去的年代,包括《隨想曲》、第一、第二號木管小奏鳴曲、雙簧管協奏曲、豎笛與巴松管二重協奏曲,以及《死與變形》,均與同時代的十二音列或序列主義背反,反而退回到調性音樂的世界,史特勞斯用十八世紀的配器法,與看似簡單又純粹的室內樂表現,做成難以捉摸的混合,其目的在於觸忤其同時代的前衛派,與他覺得愈來愈沒意思的聽眾,借用薩依德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倒退。此殆屬流年暗中偷換,對過去不帶疑問的懷舊。
薩依德指出,史特勞斯之所以採取十八世紀的音樂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抗華格納的《尼伯龍根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意涵。史特勞斯試圖遠離華格納式那種氣勢橫掃一切,情緒激蕩的無止境旋律。而當文化研究學者推崇某種作曲形式時,此類作品常不為流俗所喜。因此,相較而言,《莎樂美》和《伊蕾克特拉》顯然較不受愛樂者青睞,一般愛樂者寧耽溺於《玫瑰騎士》的優美旋律(Glenn Gould/ Johann Christian Bach: Goldberg Variations/ CBS IM 37779, c. 1982),沈浸於十八世紀的宮廷嘻鬧,一如莫札特通俗劇《女人皆如此》之普受喜愛。
史特勞斯的回到十八世紀,一如藍培杜莎的《豹》(The Leopard)回到往日時光,在這本小說中,幽暗、破碎的死亡記事,癱瘓與衰朽無所不在。《豹》描述西西里一位沒落親王法布里奇歐(Don Fabrizio)的故事,藍培杜莎書寫技巧的主要創新之處,在於敘事組織結構不連續,是一系列離散但細心經營的片斷或插曲,有時則是環繞一個特定時間而組織,如《豹》第六章〈舞會:1862年12月〉,成為維斯康提電影《浩氣蓋山河》(Gattopardo Il)中最有名的場景。維斯康提將《豹》改編為《浩氣蓋山河》,而〈舞會〉這一幕呈現的豪華場景,卻留給觀眾最深刻的印象。維斯康提用豪華的電影場景,表述義大利南方式微史的集體呈現,成為一種弔詭之對立。薩依德指出,藍培杜沙的《豹》乃係對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南方問題〉的回應,而這個回應卻是沒有綜合、沒有超越,也沒有希望的。藍培杜莎在《豹》中用易讀可解的形式表達,而非如阿多諾和貝多芬般千方百計要讓人難以了解。然而當維斯康提以北方的電影工業呈現南方主題時,所造成的錯亂,卻又變成娛樂消費的對象。我相信一般觀眾走進電影院看《浩氣蓋山河》時,感受到的並非貴族的沒落,南方的腐朽與衰敗,反而是豪華的布景,華麗的衣著和歌聲舞影。雖然藍培杜莎小說裡幾乎每一頁都是死亡的蔭影,但到維斯康提的電影裡,卻呈現另一種夕陽餘暉,如此燦爛而美麗。或許我們可以說維斯康提的《浩氣蓋山河》是對藍培杜沙的刻意誤讀;寶琳.凱爾在《紐約客》的贊賞文章,則是對《浩氣壯山河》的另一次誤讀;從破敗到華美的貴族外在形式,一種經過誤讀程序,產生的奇異結果。而買票走進電影院的觀眾,對《浩氣蓋山河》則是另一種誤讀。由於雙重誤讀產生的結果,恰與藍培杜莎的初衷背反。有趣的是,我們看到薩依德對貝多芬、史特勞斯、莫札特、藍培杜莎、維斯康提所做的討論,均有別於一般大眾的認知,薩依德所指涉的支離破碎、倒退、與社會脫節、反時代潮流,種種晚期風格特質,在大眾文化中往住是另一種解讀。那麼,薩依德揭示的文化現象,究竟是走在時代之先,或與時代背離,是一個饒富興味的問題。
討論惹內的篇章,是《論晚期風格》最貼近二十世紀末的。惹內因為對巴勒斯坦和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支持,使他站在歐美中心論的對立面。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中,惹內公開支持「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Algérie pour les algériens);故爾法國以民族主義之名,於1830年將阿爾及利亞納為屬地時,阿爾及利亞則以民族主義之名抵抗法國,而兩個民族主義都非常倚重「身分」政治。「法國的阿爾及利亞」(Algérie française),及其對應的「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反應的是身分的肯定,戰士和到處彌漫的愛國主義,都在同心同德的民族主義名義裡動員起來。
惹內和巴勒斯坦的關係斷斷續續,其作品《愛的俘虜》支持巴勒斯坦人1960年代末期的抵抗,直到他1986年去世,猶一本初衷,故惹內支持巴勒斯坦獨立之鮮明立場不容置疑。而《屏風》在阿爾及利亞反抗殖民統治的高潮期間,支持阿爾及利亞的反抗運動。雖然惹內在《屏風》裡攻擊法國,很可能是在抨擊那個審判他,將他禁閉於梅特雷(Le Mettray)等地的政府。但在另一層次上,法國代表一種權威,所有社會運動一旦成功就會僵化而成的權威。而惹內的西方/法國/基督教身分,和一種完全不同,完全屬於他者的文化搏鬥,可謂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在《愛的俘虜》裡,惹內的基調為反敘事和斷裂,在巴勒斯坦人追求重生的起義裡,如同阿爾及利亞的黑豹黨,向惹內顯示一種新語言,這種新語言並非條理井然適宜溝通的語言,而是一種驚人的抒情語言,隨處可見的切片、斷裂和背叛。然而當惹內對巴勒斯坦革命心懷至深的同情,且認為自己身、心與精神都在其中時,惹內卻自覺自己是個冒牌貨,一種永遠衝撞界限的人格。事實上,可能就是在這重意義上,薩依德將惹內列入晚期風格討論,一種斷裂和失序的、幽黯的、不合時代的,與社會價值背反的風格。在惹內作品中,死亡以折射的方式,反諷的面貌出現。如果閱讀是愉悅的,那麼惹內的晚期風格顯然反其道而行,死亡意象為其主要書寫。惹內的晚期風格,風調未調和而激切強烈,災難帶來宏壯危險,細膩抒情的雄偉感情,如此對立而不和諧。
這種斷裂的、失序的、與時代背反的風格,在《魂斷威尼斯》有清楚的軌跡可尋。湯瑪斯.曼的《魂斷威尼斯》雖屬其早期之作,卻洋溢秋意,甚或時而流露輓歌之氣,呈顯出華美與衰頹的對立。而布列頓的《魂斷威尼斯》歌劇,藉音樂語言,將不諧和的成分融接成一種混合體,在酒神戴奧尼索斯與太陽神阿波羅之間相互鑿枘,彼此鬥爭。布列頓在《魂斷威尼斯》歌劇中,雖未走進意義滅絕之境,但也沒有解決衝突,因而壓根兒不曾提供任何救贖、信息或調和。
薩依德所揭示的「晚期風格」意涵,既超越時代又被時代淹沒,在大膽與驚人的新意上,晚期風格走在它們時代的前面;而在另一方面,它們比它們的時代晚,它們返回被無情前進的歷史遺忘或遺落的境界。貝多芬的晚期風格,與其同時代的社會秩序形成矛盾、疏離的關係。在阿多諾、莫札特、史特勞斯的作品裡,切片、斷裂、背叛、語言的意涵,隨處可見;在藍培杜沙、維斯康提的作品裡,死亡的主題不斷復返;惹內晚期風格的死亡意象,令讀者感傷。死亡暗損,但也奇異地提升他們的語言和美學。
薩依德的文字雄辯滔滔,使《論晚期風格》充滿閱讀的樂趣。然而閱聽人在閱讀過程中,並非彎下腰就能隨手摘到玫瑰。而必須經過文字的冒險旅程,依循薩依德的指引,穿越危崖深壑,方能採擷山谷裡的百合。
2010年3月4日 寫於政大340221研究室
****
我十六歲,就閱讀彭先生翻譯的德國文豪,湯瑪斯曼的,魔山。真正是扛頂之作。感謝彭先生。
楊照先生在誠品講堂開了《浮士德博士》經典閱讀,慣例的5堂上完,應學員之請旋又加課4堂,1、2百人拜讀彭先生譯書數月,年底前課程才結束。謹向彭先生致敬。
謝謝老大介紹,光「脈絡」與「框架」二詞,足以不朽矣。2009 翻譯之《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也是幸而得能人譯之。
---
驟聞譯界前輩過世,痛哉。兩年前曾聆聽前輩分享譯事,雖不盡然百分百贊成,但前輩謙沖為懷的風采,自學德文有成的毅力,令吾難忘。
世事無常,切莫為小情小怨所絆,想做的、該做的,把握當下,即時去做!
 A report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Warren E. Buffett is in talks to buy as much as 20 percent of Bear Stearns has raised the specter of the investor's 1987 deal to take a 12 percent stake in Salomon Brothers. But TheStreet.com suggested that a Bear investment would go against the grain for Buffett.
A report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Warren E. Buffett is in talks to buy as much as 20 percent of Bear Stearns has raised the specter of the investor's 1987 deal to take a 12 percent stake in Salomon Brothers. But TheStreet.com suggested that a Bear investment would go against the grain for Buff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