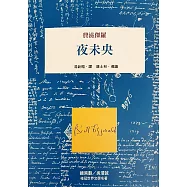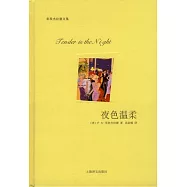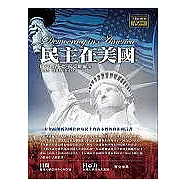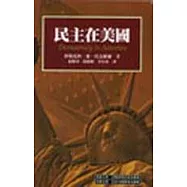周作人手稿《關於路吉阿諾斯》
1965年4月26日,周作人寫定遺囑:「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爲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即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值得留意的是在其「一生文字」之外,特別強調自己的翻譯工作。我曾說,自1943年底揭櫫「倫理之自然化」與「道義之事功化」後,周作人就進入了「總結時期」,寫了《我的雜學》、《夢想之一》、《道義之事功化》、《凡人的信仰》、《過去的工作》和《兩個鬼的文章》等一系列文章,至1949年寓居上海時給周恩來寫信,乃吿完成。此後雖然創作上還有整整一個晚期,但正如廢名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談到周氏時所講的「老年人都已有其事業,不能再變化的」,總的來看不復有新的進境。
但幾乎與「總結時期」起始同時,周氏着手翻譯日本文泉子著《如夢記》,在自家主編的《藝文雜誌》上連載,至1944年9月登完,這距其前一部譯著《希臘擬曲》出版,已有十年之久。繼而他更明言自己行將有所轉型:「不佞少時喜弄筆墨,不意地墜入文人道中,有如墮民,雖欲歇業,無由解免,念之痛心,歷有年所矣。或者翻譯家可與文壇稍遠,如真不能免爲白丁,則願折筆改業爲譯人,亦彼善於此。完成《神話》的譯註爲自己的義務工作,自當儘先做去,此外東西賢哲嘉言懿行不可計量,隨緣抄述,一章半偈,亦是法施,即或不然,循誦隨喜,獲益不淺,盡可滿足,他復何所求哉。」(《〈希臘神話〉引言》)
然而,他翻譯的《希臘神話》只在《藝文雜誌》連載了三回即吿中止,《如夢記》亦未能如其所願以單行本發行。及至身系南京獄中,「我把一個餅乾洋鐵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當做小桌子,翻譯了一部英國勞斯(W.H.D.Rouse)所著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其時浙江五中舊學生蔣志澄在正中書局當主任,由他的好意接受了,但是後來正中書局消滅,這部稿子也就不可問了。」直到他交保釋放,前往上海暫住,其間將英國韋格耳所著《萊斯沃斯的薩福,她的生活及其時代》編譯爲《希臘女詩人薩波》,「改業爲譯人」才真正實現。「書編成後將原稿託付康嗣羣君,經他轉交給上海出版公司,後來鄭西諦君知道了,他竭力慫恿公司的老闆付印,並且將它收入他所主編的文藝復興叢書裏邊。」(《知堂回想錄》)早在抗戰勝利後不久,鄭振鐸就發表過《惜周作人》一文,有云:「我們總想能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從事於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周氏日後感慨:「古來有句話,索解人難得,若是西諦可以算是一個解人,但是現在可是已經不可再得了。」此書於1951年8月出版,印三千冊。周作人從上海回到北平,重新翻譯《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譯本取名《希臘的神與英雄》。「譯好後仍舊寄給康君,由他轉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承李芾甘君賞識,親予校勘,這是很可感謝的。」(《知堂回想錄》)此書於1950年11月出版,共印五次,合計一萬零六百冊。以上兩書均署名「周遐壽」——「遐壽」與其本名「作人」同出《詩經》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如果說上述鄭振鐸和巴金之舉或許多少帶有個人色彩的話,那麼,1950年1月出版總署署長葉聖陶造訪周作人請他翻譯古希臘作品,就如周氏所說是「我給公家譯書的開始」了。1951年2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報吿毛澤東:「周作人寫了一封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房屋(作爲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封信給周揚,現一併送上。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爲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批示:「照辦。」(《胡喬木書信集》)據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的樓適夷說:「他要求用周作人的名義出版書,中宣部要他寫一篇公開的檢討,承認參加敵僞政權的錯誤。他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但不承認錯誤,認爲自己參加敵僞,是爲了保護民族文化。領導上以爲這樣的自白是無法向羣衆交代的,沒有公開發表,並規定以後出書,只能用周啓明的名字。」(《我所知道的周作人》)——這在周氏實際上是「以字行」,應該說是最接近於本名的了。
1952年7月至8月間,周作人的譯稿《伊索寓言》、《希臘神話》及歐里庇得斯三部悲劇被移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自此以後我的工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首先是幫助翻譯希臘的悲劇和喜劇,這是極重要也是極艱巨的工作,卻由我來分擔一部分,可以說是光榮,但也是一種慚愧,覺得自己實在是『沒有鳥類的鄉村裏的蝙蝠』。」(《知堂回想錄》)1953年12月,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周作人政治權利。他對此反應相當平靜,當天下午即起手翻譯歐里庇得斯的劇本《厄勒克特拉》。該項判決似乎並未發生效力,次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周作人翻譯的作品。出版社起初計件付酬,從1955年1月起更改稿費結算辦法,每月預支二百萬元(舊幣制,合二百元),自此周氏始有固定收入。1960年1月至1964年9月,更增至每月四百元。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起,出版社停止預支稿酬。同年7月8日周氏日記云:「譯書得二紙。」是爲絕筆,最後所譯之《平家物語》未能完成。其間周氏共有下列譯著在內地出版:
《阿里斯托芬喜劇集》(與羅念生、楊憲益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11月第1版,精裝本印四千五百冊,道林紙精裝本印九百冊。
《伊索寓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2月第一版,平裝本印二次,共五萬三千冊;精裝本印一次,三千冊;1963年1月第二版,平裝本印一萬五千冊,精裝本印一千四百冊。
《伊索寓言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3月第一版,印五萬五千冊。
《日本狂言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4月第一版,平裝本印一萬二千冊,精裝本印一千冊。
《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與施蟄存合譯),作家出版社1955年4月第一版,印一萬七千冊。
《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一)》(與羅念生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精裝本印四千冊。
《烏克蘭民間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第一版,印二次,共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冊。
《俄羅斯民間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第一版,印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冊。
《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二)》(與羅念生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11月,精裝本印三千六百冊。
《希臘神話故事》(即《希臘的神與英雄》),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第一版,印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冊。
《歐里庇得斯悲劇集(三)》(與羅念生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精裝本印二千四百冊。
《浮世澡堂》,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印五千冊。
《伊索寓言選》(注音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6月第一版,印七萬冊。
《石川啄木詩歌集》(與卞立強合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1月第一版,平裝本印七千七百零五冊,精裝本印三百零五冊。
《古事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2月第一版,平裝本印五千冊,精裝本印二百冊。
而周作人已經交稿,生前未及付梓的尚有幾種。——最初當是困難時期紙張缺乏之故,繼而則如周氏自己所說:「古典文學是冷貨,所以不大印行。」(1965年4月21日致鮑耀明)除個別遺失外,所譯《希臘神話》、《浮世理髮館》、《枕草子》、《路吉阿諾斯對話集》和《平家物語》均在身後問世。
1966年2月10日,周作人給時居香港的徐訏寫信,回顧抗戰爆發後他先在北平「苦住」,終於出任僞職之事,有云:「可是我也並不後悔,不但是後悔無濟於事,而且現在這十多年來,得以安靜譯書,也是我以前未曾有過的境遇。以前以教書爲職業,沒有餘暇做翻譯的工作,現今是工作與職業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譯的書於今才得實現,即如希臘路吉阿諾斯(英國人叫他Lucian)的對話二十篇,總計有四十七八萬言,這乃是我四十年來的心愿,在去年裏總算完成了。」雖雲「給公家譯書」,選目卻系出版社與周氏商議決定,至少他可以接受,更多則是他希望翻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神話》、《狂言選》、《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等,均在此列。而《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古事記》、《枕草子》等,亦屬譯界難以替代之作。這回我所編訂的《周作人譯文全集》出版,共十一卷,七千多頁,有三分之二內容完成於1949年至1966年之間。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氏一再強調的《路吉阿諾斯對話集》,他的別種翻譯具有文化價值或文學價值,此項翻譯則另具思想價值。周作人以「疾虛妄」和「非聖無法」來概括路吉阿諾斯的精神,而他亦以此自許;路吉阿諾斯旨在顛覆既有的價值體系,與周氏所說「我從民國八年在《每周評論》上寫《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兩篇文章以來,意見一直沒有什麼改變,所主張的是革除三綱主義的倫理以及附屬的舊禮教舊氣節舊風化等等」,在思想方向上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有如一部「知堂晚年定論」。作爲那一年代精神領域的異數,周作人譯《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或許可與陳寅恪著《柳如是別傳》相提並論。
周作人晚年翻譯的作品,在當時均非熱門,談不上曾經產生多大影響。周作人當年還在遺囑「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一句後面,添加一筆:「但是阿波[羅]多洛斯的神話譯本,高閣十餘年尚未能出板,則亦是幻想罷了。」不過他畢竟譯出了這些作品,並且留存了下來。周作人的譯作,包括他所寫的分量極重的注釋,誕生於一個愈來愈意識形態化,乃至完全泯滅個人趣味、風格和思想的年代,它們卻全不沾染意識形態色彩,與他同期所著《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木片集》和《知堂回想錄》等等一樣,所說的都是他本人感興趣、知道而且想說的話。時至今日,它們仍然葆有生命力,皆爲傳世之作。而創作和翻譯了這些作品的周作人——雖然已在六十四歲到八十一歲之間,即一位退休老人的年齡——其實是當時取得最大文學成就的一位。相比之下,他的同代和後輩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廢名等,如今看來在同一時期都沒有留下什麼像樣的作品。
舒蕪作《周作人概觀》有雲,周作人當年如果南下,「譬如說到了昆明的西南聯大,說不定會成爲抗戰文藝中一個消極的力量,勉勉強強地跟到抗戰勝利」。之後又會怎麼樣呢?1949年之後,以周作人的政治身份,他不止是被邊緣化,簡直是被摒於邊緣以外了,然而,他也因此得以躲過「文革」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就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也沒有他的份兒,根本拒絕他參與,更不要求他表態。當然周作人最終仍然未能逃脫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在遭到紅衛兵毒打並被趕出住處數月後,於1967年5月悲涼地死於一間小廚房中。假如周作人不是這種政治身份,或者具有這種政治身份的不是具體他這個人,那麼,「十多年來,得以安靜譯書」將會令人難以想像;又假如1949年他沒有留在大陸,而是像徐訏或曹聚仁那樣去了香港、澳門——以周作人的政治態度,不可能去台灣——雖然最後能得善終,但是恐怕不一定有條件一本接一本地翻譯古希臘和日本古典文學作品。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儘管周作人此番際遇,實乃絕無僅有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