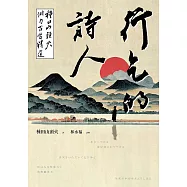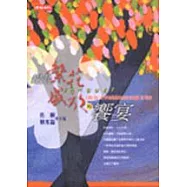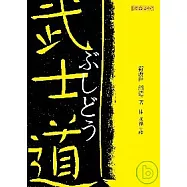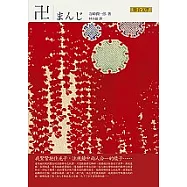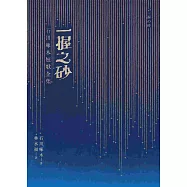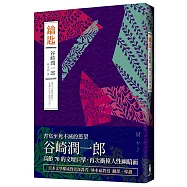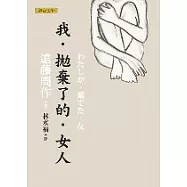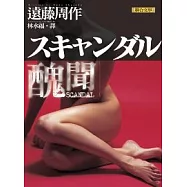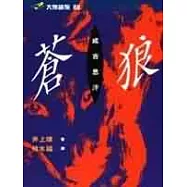「華人世界裡流傳的《格理弗遊記》,可以說是經典的幸、與不幸。」單德興有些無奈地說道。幸,是這部英國文學經典幾乎無人不知;但不幸,則在於它廣為流傳,卻被認為沒必要再仔細閱讀。更諷刺的是,華文世界通行的版本經常是被「節譯」或「誤譯」之後的樣貌,而不是全貌。
單德興受邀演講時,常以「你看過《格理弗遊記》嗎?」開場。幾乎所有人都表示讀過翻譯、改寫、漫畫或動畫的版本,但從第一、二冊的小人國、大人國,問到第三、四冊的島國、馬國,閱讀過的人數愈來愈少,最後只剩下英語系學生讀過原文版本。

大眾看過的《格理弗遊記》,往往只是第一冊的小人國。 圖│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格理弗遊記》原來有四冊,是愛爾蘭出生的綏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用來諷刺人性、英國時政與權貴的作品。
在第一冊第三章裡頭寫道,小人國國王將三種不同顏色的細絲線,賞賜給一種類似凌波舞舞技最佳的三位表演者。表現靈巧、跳躍、爬行時間最久的前三位,分別賞賜藍、紅、綠絲線。單德興指出,不同顏色的絲線,分別影射當時三種頒予爵士的勳章:藍色綬帶的嘉德勳章、紅色綬帶的巴斯勳章、綠色綬帶的薊勳章。
"用凌波舞表演取得絲線,其實是譏諷國王用人非選賢與能。"
「凌波舞高手的筋骨要很柔軟,是在影射沒有骨氣的人才能得到寵愛、成為高官嘛!」單德興笑著說。
但也因為暗示得太明顯,出版商擔心這段文字會得罪當道,因此在出版的時候將絲線的顏色改為紫色、黃色還有白色。顏色一改,寓意煙消雲散,多虧單德興參考不同的英文註釋本與相關研究,在譯注中加以說明,中文讀者才能重新瞭解作者綏夫特的用心,以及其他中譯本可能根據的英文版本。
被視為愛爾蘭民族英雄的綏夫特,其長達四冊的諷刺文學經典介紹到中文世界後,幾乎沒有辦法以真面目示人。單德興發現,中文世界最早的三個譯本中,《談瀛小錄》(同治11年〔1872 年〕)、《僬僥國》(後來改名為《汗漫游》,光緒29年至32年〔1903 至 1906 年〕),先後在《申報》和《繡像小說》以連載的形式刊出,直到林紓與魏易(另一說是曾宗鞏)合譯的《海外軒渠錄》才首度以專書的形式出版(光緒32年〔1906 年〕),而且出版者都位於開風氣之先的上海。
但在流傳的版本中,大多經過改寫、甚至腰斬得面目全非。即使是逐句翻譯,錯誤與誤解也屢見不鮮。單德興舉第一冊第一章為例說明:“ Leyden:There I studied Physick two years and seven Months, knowing it would be useful in long Voyages ”。其中 “ Leyden” 是荷蘭西南部的城市,林紓直接使用音譯──來登,卻沒有加以註解,讓當時的讀者只得到「外地城市」的模糊訊息,而不知該城市在當時歐洲的文化與思想上的重要性。
"還有 “ Physick ” 一詞,早期被誤譯為「格致」,也就是現代的物理學。但在綏夫特的時代,該詞指的是「醫學」。"
學習科目一變,《格理弗遊記》主角船醫的身分,就變成了物理學家,在長途航行中該如何發揮所學有些令人困惑。由此可見,翻譯時被誤解的細節,對語句、甚至是文意暗示卻有極大的影響。
翻譯要接近原文或譯入語?
對翻譯要求完美,幾乎是種苛求。不論是貼近作者原意與表達方式的「異化」策略,還是翻譯得通順、易讀的「歸化」手法,都會面臨挑戰。
"余光中曾說:「譯無全功」(“Translation knows no perfection”)。翻譯沒有完美的時候,但不能因為無法達成而卻步不前。"
單德興認為,從最高標準來看,「完全忠實」是不可能的。2017 年余光中的兩本譯詩集──《守夜人》與《英美現代詩選》推出修訂版。就算余光中是翻譯自己的作品,《守夜人》前後還是有三個版本,以期精益求精。原因在於每種語文都有特殊的形、音、義,尤其是譯詩,文意跟音樂性很難兼顧。
即便是不可能的任務,單德興依然認為要在能力與時間的許可下,用「序」帶出這個文本的時代背景、文化脈絡、作者地位、作品特色等等,幫助讀者理解文本所產生的時空環境;並於譯文中加上「註解」說明原文詞彙的考證、可能的意涵、翻譯時的考量……,並帶入歷史與文化背景,以期達到異文化傳達與溝通的作用。
單德興引申余光中的「演員」比喻,表示「翻譯文本的時候,譯者是一個忘我的演員,要入乎其內;註解文本的時候,包括知識、見解與立場,要站在舞台外面,客觀解說,出乎其外。」因此,譯注者既是演員,也是劇評家。單德興說,註解可以補充譯文無法傳達的脈絡,加上再三修訂,盡量將翻譯做到忠實、通達、充實。
長期研究、並親身實踐翻譯的單德興強調,翻譯絕不只是把文本移植到另一個語文,還牽涉到原作者與譯者雙方的文化。讀者透過譯注者體現的自身文化脈絡,以及他所呈現的原作者與作品的文化脈絡,有機會深入瞭解譯注的經典,形成一種「雙重脈絡化」 (dual contextualization) 的模式。
譯者動輒得咎的尷尬處境
如《格理弗遊記》般被誤譯、誤解,卻又備受歡迎的案例史上罕見,但翻譯所遭遇的困難、錯誤與挑戰卻從來沒有少過。單德興引用帶有懷疑、貶斥的義大利諺語,說明譯者的處境:
"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譯者,反逆者也"
「反逆」指的是違背原作的意義。撇開誤譯不說,翻譯過頭或不及都可能被視為逆反。翻譯得順暢,可能被質疑過度遷就本國語言,而犧牲原文的特色與含意;然而若是措辭、語法貼近原著,則往往會被批評為文句生硬、文意不通。
翻譯英文詩的時候,尤其難以拿捏。古典英詩有自己的格律,呈現於韻腳、節奏、行數、詩行長度,貼近原文的中文翻譯,有可能讀起來比較呆板。為了湊齊一行十個字,可能會顯得不自然。與其為了保存形式而犧牲文意,不如在中文字數和韻腳上保留些彈性。「即使詩的格律無法完全保留,至少要讓讀者知道原意,以及原文是有押韻的。」執意押韻卻譯成打油詩,反而得不償失,單德興這樣分享余光中的多年經驗之談。
無論是翻譯一般書籍或詩作,譯者絞盡腦汁,將原文文本轉化之後,讚嘆與榮耀常盡歸於作者,譯者彷彿隱形一般不被看見。然而,當翻譯有缺失時,譯者責無旁貸,成為眾矢之的。這是翻譯人常面臨的窘境。此外,臺灣社會普遍不重視翻譯,許多人以為只要有 Google、字典在手,翻譯不是大問題,甚至會有「無法創作,才從事翻譯」的刻板印象。
面對這種刻板印象,單德興略帶挑戰地說:「找兩段文字,自己動手翻譯看看。」即使是對話的文字也不一定比較容易。藉由翻譯簡短文字來揣摩、體驗翻譯的過程與感受,可能就會對翻譯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作者」是文字的創作者,從無到有,生產一個文本;「譯者」則是文字的轉化者,將一個語文的作品轉化成另一個語文。不僅如此,將文本用另一個語文再現,也是透過文本引介「異文化」,因此,譯者同時扮演了文本的「再現者」、文化的「中介者」兩個角色。從文字、文本、文學到文化,翻譯是超乎想像,龐大而複雜的工程。當被問到是否能分享「翻譯」的經驗,單德興語重心長地說:「說來話長,就像許多網路心得文開頭會寫『文長慎入』。」
翻譯,讓外文作品更容易閱讀
單德興提到,當初是因為就讀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如今改名為英國語文學系)而接觸到翻譯,很感興趣,大二時參加當時余光中(系主任)舉辦的全校翻譯比賽,一舉得到首獎,更增加信心。「那可說是一生的轉捩點,不然會不會多年從事翻譯我也不曉得!」
之後單德興進入中研院,在研究歐美文學、比較文學之餘,將翻譯當作志業。協助策劃並參與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嚴謹地翻譯《格理弗遊記》,除了學術譯注版之外,並有普及版。此外,也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從事翻譯研究以及其他專業服務。

「如果翻譯當成興趣來投入,那很好。但如果要將翻譯當成職業,社會對譯者的態度和待遇都欠佳,要先有心理準備。」單德興提醒。 圖│研之有物
單德興認為,想要從事翻譯,熟悉「譯出語」(原文)跟「譯入語」(譯文)是基本條件,再來是翻譯的基本觀念與技巧。即使中、外文能力良好如魯迅,但他的翻譯理念主張「硬譯」,譯出來的作品現在幾乎沒人看。而在機器翻譯愈來愈發達的時代,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一個輕易會被「人工智慧」取代的譯者,也就是翻譯的題材、內容不能像型錄、使用手冊那樣不必花費心思和技巧。譯者,既是易者,也是益者。
單德興用此句點出譯者對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這可貴之處也是只有「人」才能勝任。
「易」,兼具易文改裝,變得容易與人親近之意,因為翻譯將大多數讀者無法以原文閱讀的文本,以「容易閱讀」的方式呈現;至於「益」,是指作者與讀者同為翻譯的「受益者」,而獲益最大的其實是認真的譯者。沒有翻譯,就沒有廣為流傳的世界文學,大眾也無法接觸到美好的作品,作者的才識也無法受到肯定,異文化之間更無法交流,甚至導致自身文化的孤立與枯萎。
世界可不只有《格理弗遊記》這本翻譯名作,信徒早晚研讀的宗教經典也是因為有了翻譯,才能在各地廣為流傳。其實我們早已置身在「翻譯」當中,只是鎮日接觸卻不自知,因此必須打破刻板印象、思考翻譯的重要性,並給予譯者必要的尊重。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一個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科普橋梁。